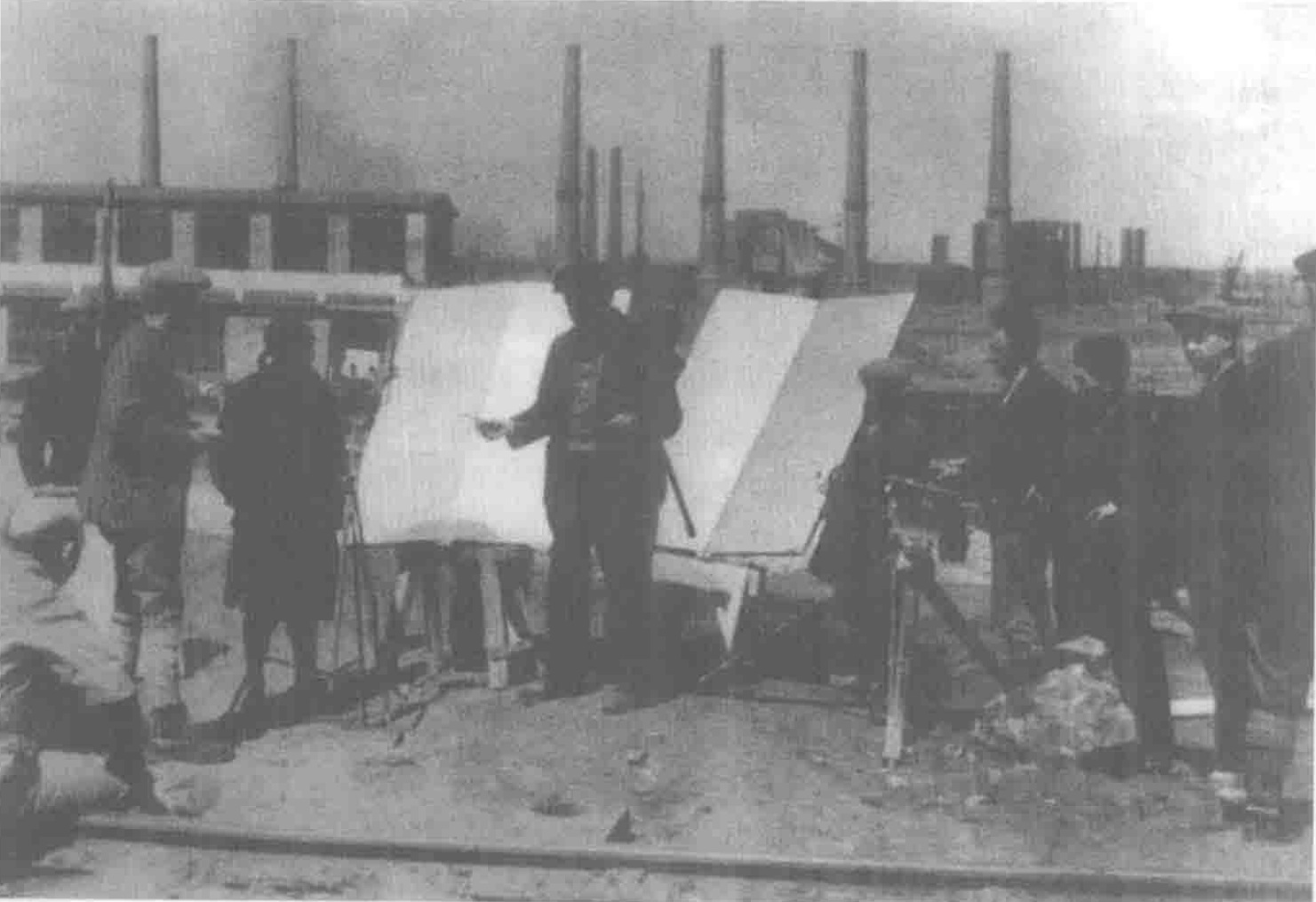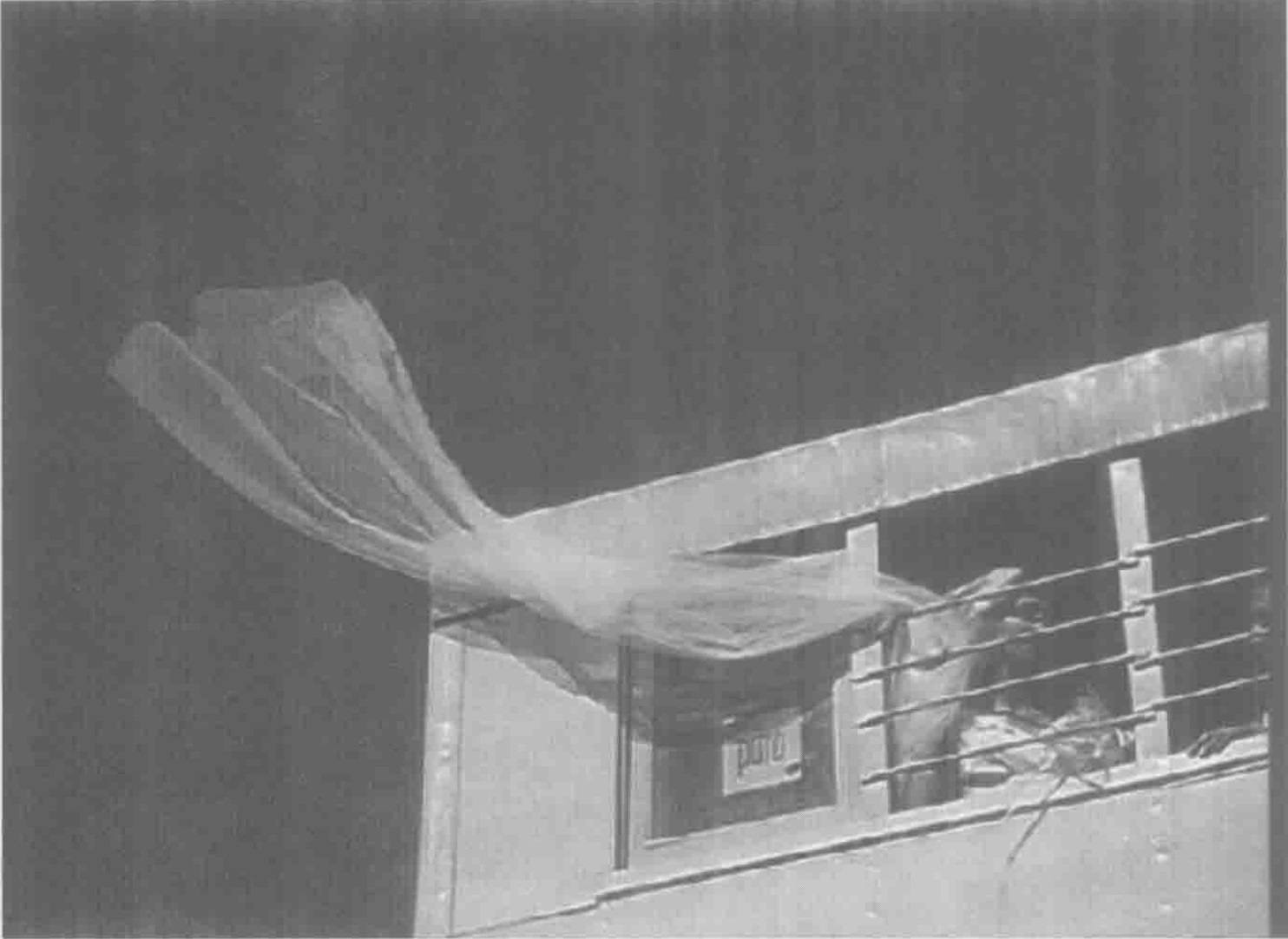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伊文思与纪录电影(1999)
伊文思电影的音乐和声音
〔法〕克劳德·布鲁内尔
孙红云 译 胥弋 校
伊文思电影中的音乐和声音,就像他作品中的其它要素一样,是一个世纪电影发展的反映。从伊文思20世纪20年代所拍摄的无声电影到他1968年开始使用同步录音摄制的影片《十七度纬线》,一直都是这样。伊文思的作品也反映了他所处的政治、地理和艺术环境。与总是容易辨认的影像不同,其作品《英雄之歌》《西班牙土地》《权力与土地》《塞纳河畔》的风格是不断发展和适应,由伊文思所访问过的不同地方的感觉所决定的。我们可以将这些作品分为三个时期:无声电影时期,35毫米有声电影时期与同步录音电影时期。
无声电影时期
无声电影时期从《对运动的研究》(1928)和《桥》(1928),接着是《雨》(1929)、《礁石》(1929)、《打桩》(1929),《我们在建设》(1929),《木馏油》(1931),《须德海》(1930-1933)开始,结束于第一版的《博里纳奇煤矿》(1933)。除了《礁石》这部半故事片半纪录片之外(因为这部电影在电影院放映时有伴奏),其他所有的原版都是无声的。这些无声电影的主要特征是视觉跟踪的音乐结构,尤其是《桥》更能体现这一点。1930年1月,当《桥》在巴黎首映后,法国先锋导演谢尔曼·杜拉克(Germaine Dulac)写到:“我看到了一首和谐的运动交响曲,节奏错落有致;我感受到了音乐的思想,敏感的共鸣充溢了那座桥;我发现了未来的视觉音乐……”这意味着。视觉影像的句法以与音乐相似的方式进行组织结构。为了发展影像句法在瞬间中的永恒关系(在音乐中,是指音符或和弦、乐器或音色;在电影中,是指由所有元素组成的镜头:面孔、姿态、建筑、景物、明暗、黑白、色彩、画格等等);意义(音乐中的音符或和弦的意义、电影中镜头的意义),以及这些元素在时间中的发展;也就是说,去实践爱森斯坦所定义的和实践过的音乐剪辑。
这种音乐写作,这种音乐剪辑敏锐表现力的强烈意识是始终贯穿于伊文思所有电影的持久的印象和风格特征。
35毫米有声电影时期
伊文思的35毫米有声电影时期开始于1931年摄制的《飞利浦收音机》(PHILIPS RADIO),该片的音乐是由娄·林奇瓦尔(Lou Lichtveld)作曲。在这部影片中,充满社会主义理想的伊文思用一种画面和声音强有力的混合,成功地将原来委托宣传飞利浦的目的进行转型。影片中他将工人们疲惫的脸、重复机械动作和飞利浦的商业产品的壮丽场景进行并置而产生意义。
早在摄制《英雄之歌》时,伊文思已经使用声音来增加视觉的效果。声音的构成体现了电影制作者政治的、社会的或教育方面的特点。伊文思像他的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一样,相信或者想要相信,一个公正的社会的出现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这也是苏联社会主义所有实现的目标。
《新地》(NEW EARTH,1934)是《须德海》的修正版,该片是伊文思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完成制作的。伊文思为影片撰写了解说词,并亲自担任了影片的解说。他开启了激进评论的大门,并确定了他对纪录电影所做的坚定选择,也就是说,在纪录影片中,电影制作者以影像和话语确定了他对人类、社会、政治的信念。
伊文思经常邀请那些与他有着共同信仰的著名作家或记者为他的影片撰写解说词,譬如,海明威为他的影片《西班牙土地》撰写解说词;达德利·尼科尔斯(Dudley Nichols)为影片《四万万人民》(1938)撰写解说词。凯瑟琳·邓肯(Catherine Duncan)为《印度尼西亚在呼唤》(1946)和《初年》(THE FIRST YEARS,1947)撰写解说词;弗拉吉米尔·帕兹纳(Vladimir Pozner)为《激流之歌》(1954)撰写解说词;以及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为《意大利不是穷国》撰写解说词;伊文思在苏联版的《博里纳奇煤矿》中公开谴责资本主义;在《意大利不是穷国》中谴责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垄断;在《印度尼西亚在呼唤》中谴责了殖民主义;在《西班牙土地》,《四万万人民》和《十七度纬线》中,伊文思充分展现人们为自由而战的精神;他在影片《初年》、《激流之歌》、《友谊的胜利》以及《和平之旅》中,显示了他对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信仰;在《塞纳河畔》中,伊文思与雅克·普雷维尔,克里斯·马克以及安德烈·韦尔代(Andre Verdet)用影像和声音一起歌唱;以及《瓦尔帕莱索》(1962)中,海港城市的声音;抑或在《南法的风》(1965)中,吹拂着大地和人们的风。
在这些政治纪录电影中,像无处不在的解说一样,伊文思从没有忘记以音乐和实际的声音来增强对观众的影响。他也从未忘记人声的影响力,如在电影《激流之歌》中,保罗·罗伯逊唱着“老人河”的声音;伊文思也绝不会忘记器乐的感染力,像在影片《英雄之歌》,《四万万人民》和《新地》中,汉斯·艾斯勒所谱写的音乐;或影片《激流之歌》中,肖斯塔科维奇谱写的音乐;抑或影片《旅行笔记》和《武装的人民》中,古巴作曲家所创作的音乐;而且伊文思也不会忽视流行歌曲在影片《西班牙土地》和《英雄之歌》中的感染力;伊文思更不会忽视实际声音的重要性,伊文思有意组织、联想和控制实际的声音与画面之间形成一种精确的同期声关系,就像他在《西班牙土地》中,利用飞机在马德里上空投下炸弹,或《四万万人民》中飞机轰炸上海时发出刺耳的不详之音。
1957年,尤里斯·伊文思重返西方,他开始把政治解说转换为社会和诗意的解说,而他仍然继续做那些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或仅仅是“人们”的代言人:塞纳河畔或瓦尔帕莱索山上的人们(《塞纳河畔》)和《瓦尔帕莱索》);以及南圭拉争取独立的人们(《南圭拉的明天》,1960)。
同步录音电影时期
越南战争再次激发了尤里斯·伊文思的斗志。《十七度纬线》是同类影片中最感人的,而且对战争乐观的谴责,并展示了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坚韧不屈,同时也呈现了他和玛瑟琳·罗丽丹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拍摄的一个越南村庄的日常生活。正是在越南,伊文思开始使用16毫米摄影机和同步录音设备拍摄纪录片。影片《十七度纬线》里没有使用音乐,而是由罗丽丹录制的战场上各种各样复杂的声音;一种非常逼真的而又很视觉化的声音。罗丽丹所录制的声音充满了影片的前景和背景,充分反映了这场战争的可怕,死亡总是不分昼夜地从天而降。然而,生存的意志和贫困国家的人民战胜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勇气,是他们顽强抵抗的证据。
在系列片《愚公移山》中,伊文思和罗丽丹运用了的手持摄影机和直接声音的一切可能手段。《愚公移山》的目的在于回答西方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疑问。该系列片12集中的每一集都是在回答罗丽丹在法国所进行的一系列关于中国问题调查中的问题。而所有的问题都设计为让中国人自己谈他们自己,就像影片《上海第三药店》中的上海人,《上海电机厂》中的工人,《球的故事》中的学生和老师,《一个妇女,一个家庭》中的北京母亲,以及《北京京剧团排练》中的京剧艺术家们等等。
《愚公移山》中严肃而准确的解说,能够给观众提供关于中国的地理、经济、社会、环境以及中国人民复杂的历史等信息。影片中的音乐、旁白以及画外音为观众提供了短暂的抒情喘息。
《风的故事》是伊文思这个时期的最后一部影片。影片中,尤里斯·伊文思思考着人生的意义,探讨了在永恒的中国“装饰风格”中,在中国的沙漠和生命的神话中,风作为世界气息的重要性。当米歇尔·波特尔(Michel Portal)的竖笛声响起,断断续续的、轻音乐似的解说,几段重复的旋律,回荡和弥漫着微弱、神秘的、内心的歌声。在这位“飞翔的荷兰人”漫长的电影生涯中,标志着人类的发展历史和电影的画面与声音技术的演变,因此,我们选择伊文思的三部影片《英雄之歌》,《塞纳河畔》和《瓦尔帕莱索》,举例分析在声音处理上所使用的不同方法。
《英雄之歌》
尤里斯·伊文思于1932年在莫斯科Mezjrabom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英雄之歌》,是他十年来艺术与政治发展的结果,该影片具有20世纪20、30年代欧洲先锋派艺术的特征。根据瓦尔特·本雅明的理论,先锋旨在回应艺术家们在历史的舞台上,努力为大众提供一种呈现,并在日常生活中适应工业社会所带来的个人经历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尤里斯·伊文思是荷兰一个资产阶级天主教商业世家之子,他在摄影器材厂(莱卡、蔡司、伊卡)学习和实习期间,伊文思在艺术和政治上的革命思想逐渐发展起来。他卷入了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那场浩劫之中,那里云集了包豪斯运动中的志同道合者:蒙德里安、布莱希特、皮斯卡托(Piscator)、弗里茨·朗、维内(Wiene)、鲁特曼(Ruttmann)以及那些引发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示威游行、社会冲突并遭到警方镇压的人们。
返回荷兰后,伊文思拍摄了影片《对运动的研究》。在旅法期间,伊文思结识了谢尔盖·爱森斯坦,并成为好友。接着,伊文思拍摄了《桥》和《雨》,这两部短片确立了伊文思作为欧洲先锋派先驱人物之一的地位,欧洲先锋派的其他代表人物还有法国导演谢尔曼·杜拉克和苏联导演弗谢沃洛德·普多夫金。普多夫金在阿姆斯特丹电影联盟放映他的影片《母亲》时,与伊文思相识。结识普多夫金对伊文思来说非常重要。就在这次放映之后,普多夫金提出,以苏联电影导演协会的名义邀请伊文思到苏联展映他的电影。在莫斯科,伊文思还见到了吉加·维尔托夫,杜甫仁科,顿斯科伊。在莫斯科,伊文思住在爱森斯坦的寓所,爱森斯坦曾在墨西哥拍过电影,并在三个月内访问过好几个苏维埃共和国。
当伊文思回国后,他受到了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工人们的热情接待。这次访问归来,鼓舞了他坚持在摄制《桥》、《雨》、《我们在建设》和《须德海》时所选择的方向。他沿袭苏联导演维尔托夫的电影道路:电影工作者就是“以摄影机的镜头来捕捉生活,就像用眼睛捕捉日常的生活场景一样”。维尔托夫熟知影像、画面和蒙太奇的力量,他曾与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和亚历山大等一起签署了一份关于有声电影中视听对位必要性的电影宣言。
1932年2月,伊文思再次返回莫斯科摄制一部能够“回答许多西方人士关于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各种问题”的影片,当时,他必须立即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选择一个有意义的题材;另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个非苏联籍导演,他与Mezjrabom电影制片厂的关系。这两个问题在当时已经由官僚主义和党的“正确思想”所决定。在普多夫金的帮助下,伊文思选择集中精力拍摄作为“社会主义前进中的最好标志”——青年运动,更确切地说,就是拍摄共青团员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建造炼钢炉。“青年与钢铁,正是我所寻找的东西。”在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写明,由共青团员(也就是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发起、实施和负责建造莫斯科城市附近的这组炼钢炉。
在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支持和监管下,伊文思组建了摄制组。摄制组中的安德耶夫·(Andrejev)担任了伊文思的助理编剧。伊文思邀请他的朋友汉斯·艾斯勒为影片制作声音。拍摄耗时三个月,伊文思大部分的拍摄是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艰难条件下完成的。实际上,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这个“社会主义新兴城市”就是在乌拉尔大草原中部搭建的一些军营和柯尔克孜帐篷;不过是在欧亚边界处一片荒无人烟的风景而已,它丰富的铁矿埋在地下。这里的工人、技师和建筑师们都是志愿者;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们年龄最大的不超过二十五岁,他们“内心坚强的意志和自豪感

《英雄之歌》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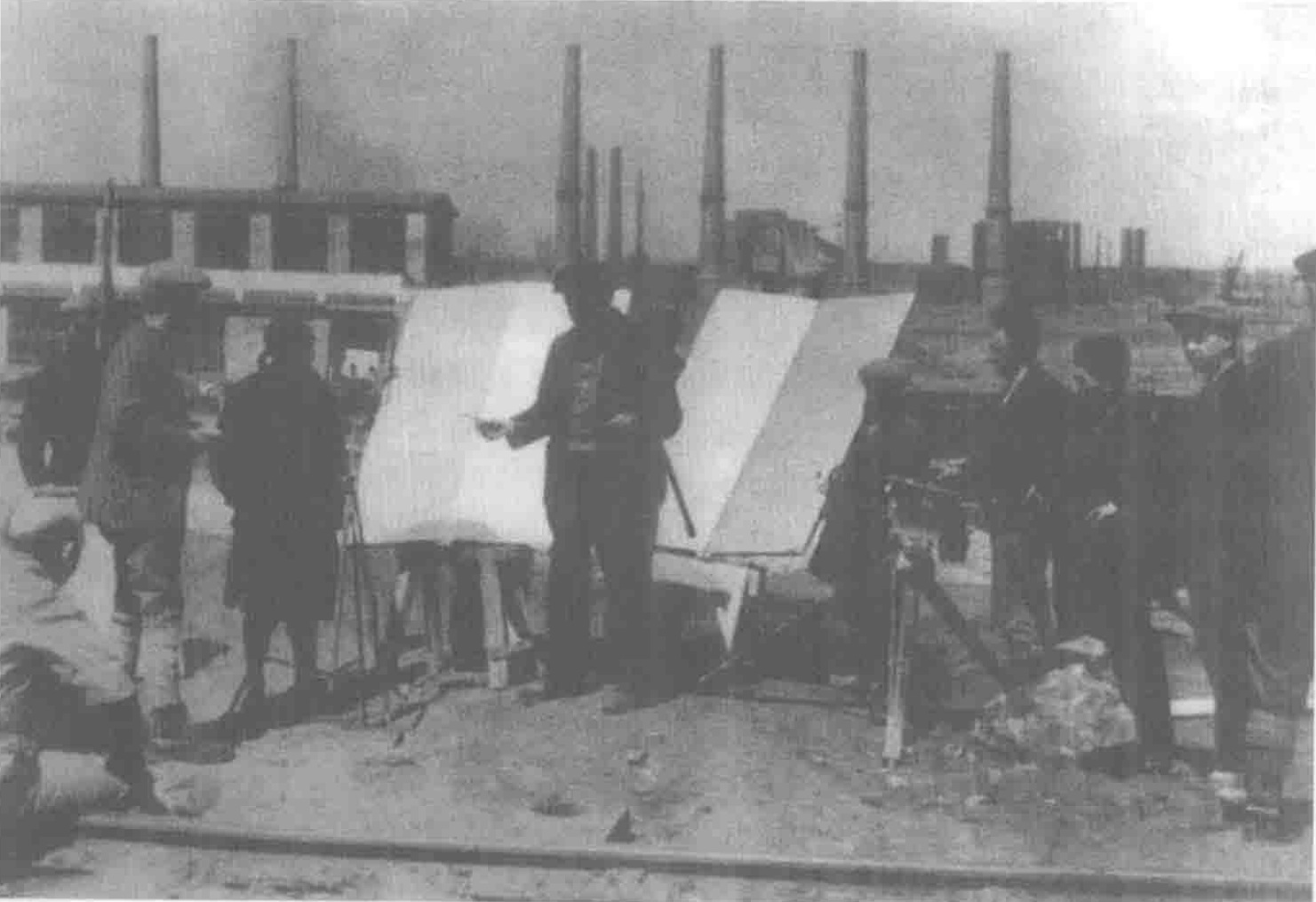
汉斯·艾斯勒(坐者)与伊文思等人为《英雄之歌》录音
促使他们豪迈地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理论,与大自然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开始拍摄不久之后,伊文思意识到影片的音乐必须要考虑“地狱般的”的现实环境,建设工地的那些声音——苏联共青团员所做的超越人类的史诗般工作的必要构成部分。于是,伊文思邀请将为影片制作声音的汉斯·艾斯勒亲自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现场加入他的拍摄工作。
伊文思和艾斯勒之间的合作,从最初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拍摄便开始了。影片中声音的每一个元素都是由汉斯·艾斯勒监督和指导完成的。几年后,汉斯写道:
我马上就意识到,我无法坐在桌旁为伊文思的这部影片谱写音乐。因此,我开始以“音乐记者”的身份工作。首先,我需要了解关于现实的复杂信息,接着我记录了这个国家一些少数民族的本土音乐和工厂里的各种声音。这项工作对我来说并非易事,因为我不习惯像一个机修工一样爬到炼钢炉顶,找到一个最佳位置上去倾听在工厂巨大的喧嚣中最动听的声音。因此,我总是为此而感到非常自豪:我能够在如此不同寻常的环境中,在胶片上记录下715米长的声音和少数民族的音乐。我工作的第二个阶段是在莫斯科完成的,在那里我谱写了这部电影的音乐,并在Mezjrabom电影制片厂进行了录制。首先,我和特雷季亚科夫(Tretjakov)同志一起谱写了苏联共青团员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之歌”。曲子非常简单:
乌拉尔,乌拉尔,
马格尼特山的城市,
那里遍地钢铁,
党说:
给我们……钢铁!
共青团员回答说:
在规定的时间里,我们一定给你钢铁!
这位自称是“音乐记者”的作曲家汉斯,和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拍摄的第一天就考虑到声音的导演伊文思,他们合作的成果是伊文思所有的作品中很独特的一部。事实上,《英雄之歌》是伊文思唯一一部从影片一开始就使用视听对位法构思的电影。影片中伊文思并没有使用解说,而是像他在无声电影中所做一样,采用字幕说明的方法。这些字幕为观众提供了理解影片所需的非常准确的关于苏联的地理、经济和政治的信息。
《英雄之歌》被认为是一部真正的声画分离的影片:画面呈现人们在建造炼钢炉各个阶段的不同工作,他们脸庞、微笑、姿态、辛勤的劳动、来来往往、交谈、片刻的休息和分享快乐。与此同时,声音解释了这个建造工作的过程:开采铁矿,提炼钢铁,炼钢炉的作用以及制造各种产品。这些通过不同工作地点的声音构成:铁锤声、钻头声、蒸汽机声、运输火车声、铁链转动声,汉斯遵循这些声乐的结构和节奏,把这些声乐与他所谱写和记录的各种器乐和声乐融汇在一起,构成一曲交响乐。这段声音以交响乐替代了特定的音乐,与画面同步出现,就像在复调音乐中叠加两行旋律一样(这里是指画面和声音),显得十分和谐(声音与画面相配)。
让我们举几个例子:
——拣钢炉的画面和声音之间的和谐(在第十四分钟以及之后)
——工人的动作和钻头声之间的和谐(在第二十四分钟时)
——妇女们将砖头传递给摆放砖头的人的画面和伴随她们动作和劳动的轻音乐之间的和谐
——工作中的口语段落和打电话声音之间的和谐
这些和谐有时是创作者对现实主义渴望的结果,而它的实现则是在电影制片厂中。例如:金属块滑过传动轴的声音,炼钢炉熊熊燃烧时,工人们奔忙的脚步声和喊话声。除了这些和谐的声音之外,影片中的声音也有因管弦乐曲而产生的分割:重音、节奏、停顿、音色;“强音”和“弱音”,“渐强”和“渐弱”。
在当地(吉尔吉斯青年面对着大草原,用长笛吹奏流行歌曲)录制的器乐和声乐,以及汉斯·艾斯勒在莫斯科谱写的音乐,它们以一种更传统的方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即强调了画面的抒情和象征意义,强调了政治信息,庆祝了共青团员的大游行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我们来分析一下汉斯·艾斯勒谱写的音乐在四个不同部分所产生的效果:
1 影片的片名和开场处;音乐非常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它展现了苏联曾遭受压迫,工人们取得前进的胜利,以及由苏联胜利凯旋进行曲发展而来的共青团进行曲。这首音乐奠定了电影的基调:决心和热情。我们很容易注意到,反复打击的节奏作为一个基调服务于影片中其他的管弦乐片段。除了片尾曲之外,节奏和旋律都是开场进行曲的变奏曲(因为片尾曲全部取自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之歌”)。
2 在招募吉尔吉斯青年时;音乐表达了苏联共青团员工作的重要性,也表现了这个年轻人的决心。
3 在一次工作大会和对共青团员工作的评估场景中;音乐表达了他们对所做工作的满意和他们集体的决心。
4 在片尾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之歌”是一首强烈的、朝气蓬勃的,而又简单的歌曲,它表达了共青团员取得胜利后的喜悦。同时具有象征意义:这些机器是为人民服务的,当然,是为共产党服务。
因此,我们目睹了一场由画面和声音交织的真正的焰火:管弦乐和声乐的节奏与由钢铁、蒸汽、姿态、运动、光影构成的蒙太奇相结合,直到最后一个画面,那个巨大的令人豪迈的炼钢炉高耸入云,释放着它自己的音乐在其中和工业气息的力量。
它是伊文思作品中非常独特的一部影片,因为它是在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发展的转折点上问世的。伊文思在影片中仍然使用字幕说明而不是采用解说的方式。《英雄之歌》的音乐、声音和基调都起到一个对位的作用。因此,观众体验到一部真正的视听作品,这与爱森斯坦在1929年为电影所下定义完全一致。
《塞纳河畔》
1957年春,伊文思抵达巴黎,这个他为了与痛苦、战争、不公正作斗争,寻求真正的共产主义而常常离别的城市。他坚信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所以他愿意去社会主义国家。他在东欧花了十年的时间拍电影,几乎都是免费摄制。但他越来越怀疑他所目睹的“社会主义建设”。而现在,他重新发现了巴黎和他的法国朋友:乔治·萨杜尔,雅克·普雷维尔,塞尔日·雷加尼(Serge Reggiani),西蒙·西涅莱,伊夫·蒙当,贝琪·布莱尔(Betsy Blair)等等。
伊文思一直深爱着巴黎、塞纳河及其林荫大道。乔治·萨杜尔给伊文思一个建议:拍摄一部关于塞纳河与巴黎邂逅的电影,用电影来表现巴黎人和他们在塞纳河畔发生的故事,以及塞纳河给予巴黎人的馈赠。于是,伊文思全身心地投入到20世纪50年代的巴黎城市中,徜徉于塞纳河畔,感受塞纳河的水流、天空、云彩、桥梁、码头、港口、熙熙攘攘的船只、历史遗迹以及人们。他开始拍摄,就像用摄影机书写一首视觉诗歌,塞纳河是主题,这首诗既活泼而又庄严,时而狂野,时而平静,还有河畔的巴黎人,水手,小商贩,河岸上的女人们,孤独的流浪者,渔夫,业余画家,年轻的情侣,嬉戏的孩子们,一切都显得那么令人兴奋和欢乐,伊文思记录了50年代所有这些巴黎流行的画而;巴黎是摄影师罗伯特·杜瓦诺(Robert Doisneau)镜头中的城市,是诗人雅克·普雷维尔用爱来赞美的城市。伊文思通过让·雷诺阿、让·维果、马塞尔·卡尔内的影像以及约瑟夫·科斯马的音乐来纪念了这个城市,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法国诗意的现实主义。
《塞纳河畔》是伊文思再次摄制一部没有明确责任的影片,伊文思摄制的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影片(指《雨》——译者注)是关于水、雨和阴沉沉的天空。后来,伊文思转而拍摄桥梁、码头、机器,劳动中人们的各种面容和姿态、妇女和儿童的脸庞和欢笑,这些是伊文思起初拍电影时的景物。《塞纳河畔》是伊文思回归他的无声电影完美的音乐蒙太奇风格。
《塞纳河畔》的画面的思路是一名搭乘着一艘小船的乘客从东到西穿过巴黎。同时又通过白天与黑夜的对比,劳动的世界与休闲娱乐的世界的对比,塞纳河东岸的工业区与宁静的田园诗般的西堤岛以及富裕而肤浅的塞纳河西岸的对比。当该片的影像拍摄结束后,伊文思开始构思影片的声音。雅克·普雷维尔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了,他不但是马塞尔·卡尔内的影片《怪事》、《雾码头》、《天色破晓》、《天堂的孩子》的编剧,他更是一位受大众喜爱的法国当代著名诗人,他笔下的文字就像画面一样,表现了塞纳河畔的巴黎和巴黎人的美好与残忍,温柔与爱情、生活、欢乐与痛苦。
尤里斯·伊文思把这部影片给雅克·普雷维尔观看。普雷维尔观看后写了首诗,并对伊文思说:“做你想做的。”这首诗的作用是与电影画面相对位:语言表达了画面所展示的内容,但又不是同步的,它往往出现在画面内容之前、之后甚至更迟的地方。这样做是加强并说明了这部影片的社会信息,而且保护了画面本身的音乐性;语言的灵感又被画面激发出来。伊文思还唤起了由普雷维尔—科斯玛(Prévert-Kosma)二人创造的银幕内外的一种魔力;普雷维尔诗的语言与歌曲《像孩子一样相爱》(Enfants qui s'aiment)和《枯叶》(Feuilles mortes)的音乐之间产生一种和谐;巴黎流行的诗歌和伪乡愁的节奏结合在一起,由钢琴演奏,单簧管或者小提琴协奏。
伊文思请求作曲家菲利普·杰拉德(Philippe Gérard)用科斯玛的风格来写音乐,也就是使音乐时断时续地与画面相伴,并延展画面和影片中诗的语言。机敏的,怀旧的,温柔的,轻快的,好玩的甚至可笑的,一曲音乐能使雨滴、流水、船只、汽车和寂静可以听得见。
影片一开始便出现了怀旧的主旋律,并奠定了整部电影的基调;舒缓的华尔兹,基于这样的旋律(fa#se re si do# re mi fa# mi si do# re do# si la# sol# si……);渐弱的手风琴音萦绕着,接着是钢琴,长笛或者弦乐器的乐音划过普雷维尔的诗歌,在音乐的回荡中,船上不时发出各种片言只语,时而消失,但它又总是在人们的脸上重现;这是一首充满爱的音乐。
《塞纳河畔》中,另一种音乐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旋律,是在巴黎地铁5号线拉斐堤岸站附近地铁飞驰而过之后。它是由短笛和长笛吹奏,跳跃而浑浊。当我们随着影片进入西堤岛,字幕提示:“这是一首来自源泉的歌,这是年轻人的声音……”这首歌是根据儿歌《这是一条小船》(Il était un petit navire)改编的,当船只经过岸边的情侣、渔夫、业余画家时,经过嬉戏的孩子们,刮胡子的流浪汉和奔跑的律师时,音乐的节奏变慢,并萦绕在巴黎圣母院高耸的尖塔、卢浮官和埃菲尔铁塔中。
欣赏这部影片的音乐,我们也不要忘了大键琴音乐的作用。作为一个换音点,它如此出乎意料地、如此幽默地为在塞纳河岸边的各种景象伴奏:拍照的模特、野餐者、到此一游拍照者、高高翘着二郎腿小憩的人,在河边遛狗的优雅女士。这首曲子从画面里一个弹奏吉他的年轻男子低声吟唱的怀旧旋律中流淌而出。另外,我们也别忘了影片中那节奏感很强、充满魅惑的爵士乐。爵士乐是当那艘船经过塞纳河上亚历山大三世桥时,一道闪电划过接踵而来的暴风雨的画面时引入的。爵士乐延伸了雷雨以及寻找避雨地方的人们的画面,而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这首爵士乐停止了,接着影片又回到手风琴的主旋律上。
《塞纳河畔》从构思到拍摄再到剪辑,用了各种元素来吸引法国人以及世界各地的观众,让他们爱上巴黎。这也是尤里斯·伊文思1957年在法国戛纳电影节获得金棕榈奖最佳纪录片奖的原因。
《瓦尔帕莱索》
1962年,在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odor Allende)的鼓励下,尤里斯·伊文思受邀来智利圣地亚哥大学“实验电影”系教授纪录电影。萨尔瓦多·阿连德是伊文思在古巴时认识的,他是当时智利反对派的领导人。伊文思接受了邀请,决定教这些没有受过训练的“当地”年轻人如何拍摄纪录电影。于是,伊文思和这些学生们一起拍摄了《瓦尔帕莱索》:
这是最繁华的港口…… 像是从巴拿马一剪刀剪断,把它放在这里……它仍然是一个港口……不是最繁华的,但它生机勃勃。它正常地运转着……在山脚下,是一个商业小镇子。山上还有另一个镇。也不算是一个镇:是几个村子联合在一起,每座山上都有一个村子。42座山,42个村子……山坡、石阶、吊桥连接着两个世界。
阳光孕育了一切,黑白画面上瓦尔帕莱索丰富的光影、山区里居民的尊严等,所有的画面是由上上下下的台阶和连接“两个世界”的索道缆车构成的。这些带领观众去领略瓦尔帕莱索的海边、港口、船只、集市、海鸥、海豚等景象;它们向我们展示了这个贸易城镇的过去和现在;它引导我们爬上或者下去,远眺或近观,摄影机从不同的角度、景别和运动来观看,瓦尔帕莱索尽收眼底:绵延的台阶、各种房子、广场、小花园、人们的游戏以及山里的表演等。
这些画面反映了伊文思对这些山里居民的温情:无论男女老少,尽管他们生活艰难,但他们却不乏欢乐、爱情和好运。突然,画面转为彩色的回忆,叙述了瓦尔帕莱索多么久远的和最近的历史都与暴力和血腥分不开。
返回法国后,伊文思剪辑了在瓦尔帕莱索拍摄的影像,并委托一人为影片写了最初的解说词。但最后,这份解说词并没有达到伊文思的期望。伊文思感到十分沮丧,在距离最后的混录还有几天时间时,他接受了好友克里斯·马克的邀请,来帮他解围。同时,他委托古斯塔沃·贝塞拉(Gustavo Becerra)为影片谱写音乐。1962年,克里斯·马克已经是一位名声显赫的电影批评家和作家了,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几部纪录电影的导演和撰写解说词的作家。于是,马克为影片《瓦尔帕莱索》撰写了非常精确有深度的,而且很有诗意却没有直接抒情的,同时不乏幽默感的解说词。克里斯·马克就像在自己的电影中一样,解说词延伸了影片的意义,延展了画面空间和影片节奏,使影片充满了智慧和广阔的视野,却显不出半点冗余,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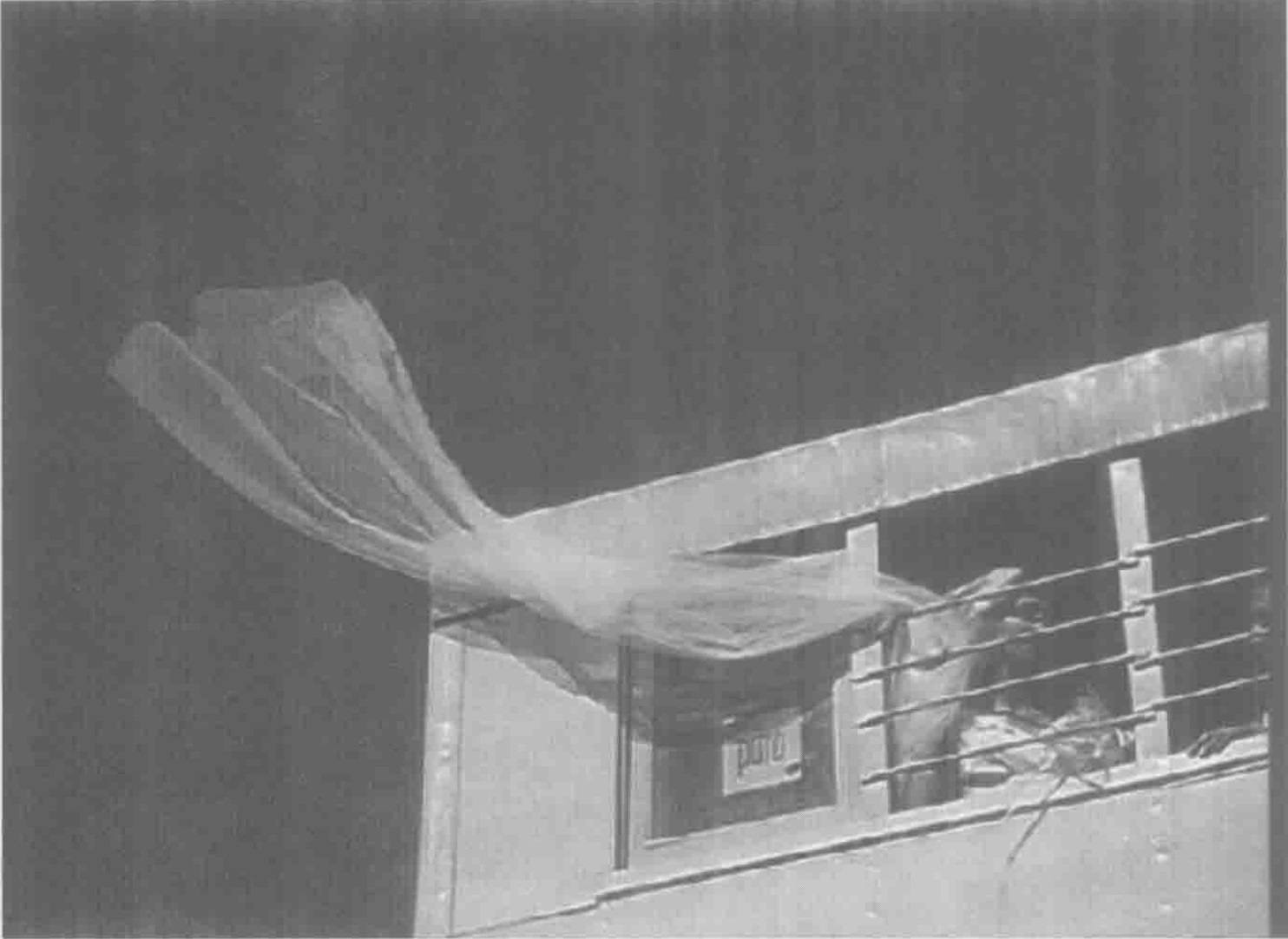

《瓦尔帕莱索》剧照:42座山,42个村子。
像他不是画面的作者一样。马克作为一个导演和作家,来为《瓦尔帕莱索》撰写解说词,他明白每段解说词开始和结束的力量在哪里。画面提供了所展示内容和各方面感到的力量;解说词的感染力则在于说明和创造了现在与过去的联系,并以幽默和轻快来控制观众的感情。
根据伊文思拍摄的画面和剪辑计划,马克为影片所写的解说词创造了一种距离:这种距离没有削弱画面的力量、美感、亲切感,乃至暴力。事实上,这种距离反而产生了一种反思,反映了克里斯·马克作为影片第一个观众观看影片时的客观性。当然,这部影片的画面和解说词之间又保持着紧密的一致性。例如:
——影片开始部分,画面:港口工人卸香蕉,解说词跟画面保持一致:“港口坐落在那里。这是最繁华的港口……”。
——画面:一辆灵车庄严地穿过阳光下陡峭的街道,相应的解说词是:“这里是瓦尔帕莱索。Val Paraiso的意思是天堂之谷,对于那些赋予这个名字的水手们来说,这里就是他们在航行的噩梦之后的触摸阳光的天堂。或者,这里是到达天堂之前的最后一步”。
——画面:阔太太们放出了她们的企鹅,对应的解说是:“瓦尔帕莱索的女人们出门时,都戴着墨镜,和她们宠养的企鹅一起敬步”。
——画面:一个长镜头呈现了港口活动和码头工人们的劳动,解说是:“这就是大海的真理”。
——画面:在嬉戏的下坡和艰难的攀登中,第一个镜头一个独腿男人在上台阶,解说:“一个独腿男人每天爬这些台阶,121级台阶,他知道有多少个,因为他总是在数。你也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和很好的记忆力。乘索道比走台阶快十倍;下坡又比上坡快十倍,下来时,你会大声地欢笑;上去时,你会上气不接下气。这是多么有趣的、筋疲力尽的、可怕的、欢乐的、不人道的、严肃的、滑稽的、奇怪的事情”。
影片《瓦尔帕莱索》的第三个结构元素是古斯塔沃·贝塞拉的音乐,根据歌曲《我们会奔向瓦尔帕莱索》(Et nous a Valparaiso)改编而来的,由杰曼·蒙特罗(Germaine Montero)演唱。这首曲子有非常诱人的节奏,在影片开头焰火照亮瓦尔帕莱索港口的画面出现时轻轻响起,回荡在影片其它部分中的画面、管弦乐和解说之间。在影片结尾处,音乐重新响起,先是温柔地低唱,伴随着优雅的长笛和竖琴声(画面是孩子们在放风筝);然后,一首新的音乐响起,由打击定音鼓的声音引入,随着杰曼·蒙特罗演唱的歌声,乐声辉煌壮丽,直至影片结束。这首歌是整部影片的主题音乐,由不同的管弦乐曲谱写而成,比画面和字幕表达意义更为微妙。
在影片《瓦尔帕莱索》中,虽然没有画面和声音的对位,但是在每个视听结构中的每个元素,每组画面、每句解说词和声音之间相互都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每个元素都不能和其它元素分开,加强了我们对影片的理解,促使我们从诗意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哲学的维度来理解这部影片。
三部电影分别用三种方式来处理画面和声音的关系;用三种方式来呈现影片要表达的口语;用三种方式选择和使用音乐。然而,这三种方式又都属于同一种风格和同一种画面音乐:伊文思的风格。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