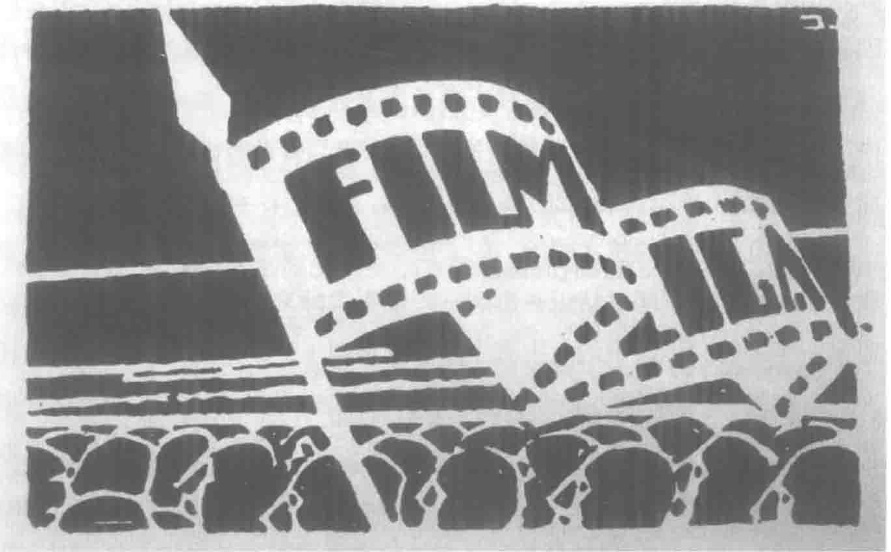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伊文思与纪录电影(1999)
第一部分:伊文思电影类型研究
运动之歌——伊文思的早期电影及先锋派创作
〔荷〕安德烈·斯图夫基斯
孙红云 李淑娟 译 晋弋 校
火车旅途中……
两条熠熠闪光的平行线
一起向远方汇聚
飞奔的车轮咏唱着运动之歌
我们都在旅途中
奔向过去?
奔向新世界!
我们匍匐世界的脊梁上
(从眼前飞速而逝
离我们越来越远)
——伊文思,1925年1月14日[1] |
“你可以知道你驾车的速度,感受飞速运动带来的喜悦,难道你不想让你的内在生命也拥有这种速度感吗?”尤里斯,伊文思不无惊讶和担心地问他的女友梅普·巴尔格里·格林,她是20年代初期伊文思最爱的女人[2]。对伊文思来说,运动不仅仅是时代的标记,也是像巴黎和柏林这些新兴大都市的繁忙和喧嚣,还是机械和电子的发明,更是一种思想状态和精神态度。他在信中继续写道:“对此我们不能有些许的三心二意。我真想大声呼喊:全速前进……我们应该像骏马一样奔腾前进。”革新和叛逆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获得新的视角和逃离父辈以及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代人的每日例行公事般生活的方法。
运动是先锋派时期的创作信条。它呼吁将艺术的想象和设计运用到思想活动的各种新情况中,包括机械的、情感的和心理的。这点也可以在伊文思早年所写的为数不多的一首诗中找到证据。就诗本身而言,说不上是一首佳作,因为伊文思曾经自己写道,1925年,他还没有找到“一种恰当的表达形式”传达他的各种情感和体验。然而,伊文思此后的所有作品都表达了:火车、旅途的感受和发现一个新世界。同时,这也是一种精神活动和有目的的寻求革新。一次又一次,每当这些短暂的感受消失,一种乌托邦思想就在他的旅行中油然而生。从开始到最后,在他所有作品中,这是伊文思一生矢志不渝的信条。
在伊文思第一部成功的先锋派电影之作《桥》(The Bridge,1928)中,一列火车停止了嘶鸣声,因为可以开合的桥这时打开,形成一个障碍,正好挡住了它的去路。在伊文思开始从事电影创作的初期,他的父亲曾经强迫他子承父业,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父亲是伊文思电影事业开始的障碍。而伊文思自己很早以前就自觉地选择过一种自由奔放的艺术家的生活。在影片《桥》中,后来桥面合拢,障碍清除,火车继续前进,胜利地喷着烟雾。机械的运动和摄影的运动结合在一起,以新的画面语言形成一种视觉节奏。绿灯亮起,火车消失在现代主义电影的结局中:以白色背景上闪烁的黑方块结束影片——这种处理方法跟马列维奇(Malevitch)的作品“黑方块”很相似,是受到德国先锋派艺术家埃格林和鲁特曼抽象画的启发。这也是伊文思本人自由解放的象征,通过《桥》这部影片,伊文思远离了父亲的生意,向电影生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1932年的影片《英雄之歌》(Song of Heroes)中,伊文思以一小段生动的未来主义小火车表达了对可能的未来工业的复杂性的一种灵光闪现,他拓展了摄影艺术与技术革新运动、社会与政治革新之间的联系。然而,也许电影中那些年轻的工人应该意识到这个趋势。1964年,伊文思在影片《胜利的列车》(Le train de la victoire)中表达了这种相似的联系,笔直的铁轨贯穿智利的国土,预示着总统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竞选专列将会推进智利的社会改革。
在伊文思最后一部影片《风的故事》(Une histoire de vent,1988)中,他和玛瑟琳·罗丽丹找到了一个简单的形象,来表达伊文思从一个大手术中活过来和濒死的体验。伊文思回到人群当中,梭巡在放风筝的孩子中间,不一会儿,一列火车隆隆地驶过中国的山河。伊文思可以再次旅行了,对这位随时整装待发的人而言,在旅途中是他一生的象征。火车把伊文思带到一个藏着神奇的风神面具的窑洞里,接着影片既是真实地又是隐喻地给了伊文思一把打开存放他所有作品柜子的钥匙。这里的风既是物理意义上的,也是精神层面上给予他持续不断变化的力量。
火车和飞机,从《桥》到《风的故事》,把世界从地理意义上连接成一个整体。同样,电影作为一种媒介在文化意义上把世界连接成统一体,推动世界文化大迁移,然而,世界的矛盾和冲突也空前极端和无情。这种鲜明的冲突是伊文思电影的本质。
令人惊奇的是,伊文思在《桥》中奉行的信条,在六十年后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中再次回归。在中国拍摄《风的故事》时,由于当地官员的短见,伊文思被禁止进入西安兵马俑实地拍摄,他就自己组建了一支兵马俑队伍(以搬演的手法——译者注)。作为导演,这位老人亲自上阵,站在军队的最前端。伊文思的这个形象参照了军事领域中“先锋”的概念,在法国军事手册中,“先锋”这个词最初是用来描述一种军事策略:即在主力部队出发作战之前,先派遣冲锋小分队来迷惑敌人,伊文思用在这里来表示先锋派运动概念的源头。没人能想到,这位老人用他的拐杖轻击地面,就能让沉睡千年早已变成化石的秦兵马俑复活了。通过这个神来之举,伊文思表明自己作为一个先锋派艺术家一贯的追求:运动与革新。最终,是艺术家的想象力使这些传统的根深蒂固的东西重新焕发生机,在看似不可能之处获得成功。它使得先锋艺术的探索形成一个完满的圆。这种探索既体现在伊文思早期的创作中,当时他视纪录电影为艺术探索的冲锋小分队,也是伊文思对新世纪的展望,因为缺乏想象力的艺术流传下来的很少。伊文思在故乡奈美根过90岁生日时,曾经这样预言:“21世纪将是一个竞争才智的世纪”。[3]
这一章描述了伊文思始终坚持的先锋艺术之路,他在先锋派艺术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先锋派艺术对伊文思而言意味着什么。
先锋电影导语
“在一个没有电影工业的国家,怎么会诞生一个电影导演呢?”荷兰资深电影批评家L.J.乔达安(L.J. Jordaan)在他1931年出版的第一部关于伊文思的专著中感到如此惊奇[4]。虽然当时距离伊文思创作第一部电影《桥》已经过去4年了,乔达安称伊文思称为最重要的电影导演,他非常惊讶,伊文思的先锋派作品能够如此之快地获得成功、欣赏和支持。这种在荷兰以及国际先锋派艺术圈中的迅速成功主要归于技术上——尤其是剪辑和摄影技术上,影片保持一种冷静和诚实。这个特点从影片一开始就表现得非常突出。而且,这种特征总是表现得恰如其分:“影片知道如何积极而具体地回答观众的各种朦胧的问题。”[5]
伊文思突然展现的这种技术革新从何而来?他是怎么成为电影先锋运动的领导者的?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论及伊文思的家庭、教育和电影训练。我们会发现在技术、政治和艺术领域,伊文思一直处于突出的位置。综合所有这些因素,伊文思的先锋艺术特质总是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焕发出光彩。
技术先锋
伊文思成长于一个非常重视观察的家庭中,同时培养了他用裸眼观察和通过镜头观察的习惯。1867年左右,伊文思的祖父威尔海姆·伊文思(Wilhelm Ivens)作为一名摄影师从德国迁居到奈美根。凭着精湛高超的摄影水平,他成为联合利华创建者尤尔根(Jurgens)家族的家庭专用摄影师,以及当时荷兰皇太后的宫廷御用摄影师[6]。伊文思的祖父、父亲和他本人,一家三代都曾在柏林职业摄影学院学习,这是当时最全面、最现代的化学和光学技术学院。伊文思的父亲(Kees Ivens)相信销售摄影器材有可能是赚钱的好途径,所以,他在荷兰开办了第一个摄影器材连锁店——卡皮(CAPI)。在该领域中,基斯·伊文思总是第一个关注新技术发展的人,并向公众演示和解释这些新的技术。他撰文说明了活动电影放映机(kinetoscope),还称之为电影的最近的先驱,并参加了卢米埃尔兄弟在阿姆斯特丹举办的第一次“活动电影”展。他曾经预言:“目前生死判定的‘活动摄影’技术的发明,将会在以后获得像印刷术一样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的地位。”[7]1902年,基斯·伊文思在荷兰展示了伦琴X射线(Roentgen X-Rays)技术。1907年,引进了卢米埃尔兄弟的彩色摄影术。早在1910年,他就建议成立荷兰摄影博物馆。

1933年,电影人伊文思在阿姆斯特丹 伊娃·贝丝奈乌摄
作为基斯·伊文思之子,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同样展现出对技术革新的钟爱,1911年,小伊文思便自己制作了一架与真实飞机大小相仿的飞机“飞翔”在他的家乡奈美根的天空。他还曾对在一家商店里看到的一台带有三脚架的百代摄影机(Pathé camera)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荷兰的集市上和电影院里常放映一些关于牛仔和印第安人的影片,尤里斯·伊文思深受影响,1912年,他编写了一个电影剧本,讲述一个发生在乡下家庭的亦庄亦谐的故事。1912年,伊文思的《燃烧的箭》或《小茅屋》(Flaming arrow or the wigwam)中,他使用了一种随机偶然拍摄的风格特征,此后,他经常反复使用这种方法:通过一些小的意外、次要事件,或者其他的不安来打断既定的叙事节奏:因为伊文思发现,正是这被打断的节奏才使观众意识到视觉节奏的存在。当时,他的父亲为他拍摄了这张站在摄影机旁的照片,并题上“电影人”(KINOMAN)的字样,这是伊文思自己都不会想到的一个预言。
卡皮摄影器材店营销埃内曼(Ernemann)以及其他厂家制造的电影放映机,小伊文思与父亲一起演示放映机的使用。“一战”期间,他观看了来自法国和比利时前线报道的各种新闻影片,他还在一幅地图上画出了战争的线路图。他之所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这点,是因为他的父亲在商店的橱窗里展示了一些通讯社刊发的前线的照片。“伊文思家族公司在战时非常地活跃,如今在它位于凡·拜赫尚斯塔特(Van Berchenstraat)的店里还保存着6张荷兰济里克泽(Zierikzee)遭空袭被毁场景的照片”[8]随后,他们在家庭影院放映了阿尔伯特·弗若斯(Albert Frères)摄制的同样关于这场“狂暴的战争”影片:“这部制作精良的影片,观众在观看时,即使‘艺术享受’的观念受到抑制,也不会逃避不看。”[9]虽然当时还没有纪录片的概念,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首次看到了大量的宣传电影,至少这些影片自称是呈现了现实:后来,尤里斯·伊文思带着摄影机奔赴五个不同的战争的前线。作为纪录电影的先锋和创始人之一,他以自己的作品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观点:“艺术享受”不应该是纪录片这种有价值的电影的一部分。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伊文思的父亲举办了一场纪实题材的摄影大赛,以此来庆贺他创建自己家族企业25周年。大赛的主题是“危机”,目的是保存荷兰在“一战”中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些情景。尤里斯被父亲任命为评选委员会秘书,他从中意识到为子孙后代们保存真实历史时刻的意义。看着由伊文思的祖父和父亲收集整理的这些关于重建家园和重大事件的照片,我们会深深感到那种严肃而不加修饰的纪录风格是深入到伊文思的血液中的。[10]
尤里斯的父亲不仅仅想建立一个家族照片资料馆,还想建立一个家族电影资料馆。从1921年开始,尤里斯拍摄了几部关于家庭聚会的影片,从摄影风格上来讲,这些影片没什么特别有意思的地方。直到1927年,我们才发现了尤里斯令人侧目的作品,他通过“司机”的眼光来拍摄汽车,拍摄他的表兄维姆的蓝旗亚轿车(这部影片是《巴黎运动研究》〔Studies of Movements in Paris , 1927〕,影片中,伊文思拍摄汽车探索摄影机镜头的运动。片中出现了一个汽车司机的主观视角,先从司机的背后拍摄前面路况,然后,透过挡风玻璃拍摄表现司机的主观视角。——译者注)同时,伊文思通过在德国职业学院的长期学习以及在德国光学厂的实习经历,磨砺了他的思想和眼界。伊文思当时在ICA摄影机制造厂基那莫(Kinamo)型号制作部门工作,该部门生产一种小型手持35毫米摄影机,伊文思就是用这款摄影机拍摄了1927年及其以后的一系列影片。回到荷兰,伊文思被聘为戴尔福特技术学院(Technical College in Delft)第一位摄影课讲师,他在那里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29年。[11]伊文思说:“最初,我的爱好和学习都是纯粹地偏向技术科学方面的。”[12]
在阿姆斯特丹的艺术圈里,伊文思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优势,这种优势恰恰来自他对技术的精通。电影,这个新的缪斯,被看作是艺术中的艺术,一种所有旧的缪斯的结合体,它仿佛成了一种神圣的或者优越的艺术形式。“对于他们来说,电影是一种神秘的事物,而这种神秘是技术创造出来的。渐渐地,我开始理解了他们对我的兴趣所在和我所呈现给他们的是什么。在他们眼中,我是个技术大师。”[13]
政治先锋
在这个家庭的自由气氛中,政治被视为通往解放的必然手段。后来,伊文思激进的政治选择与三个解放运动有关:荷兰德国移民运动;荷兰天主教解放运动;全球劳工运动。
伊文思家族属于是19世纪从德国移民至荷兰的天主教企业主家庭,他们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后,便进入社交和政治领域以提高荷兰天主教少数派几个世纪以来的没落地位。从他们的各种积极行动来看,伊文思家族不仅对提高天主教少数派的地位感兴趣,而且也谋求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这一点与其他有影响的天主教家族形成鲜明的对比。
祖父维尔海姆·伊文思是“博爱”中心委员会的成员,这个组织呼吁全社会关爱所有流浪儿童。伊文思的父亲基斯·伊文思,则被任命为“宗教与科学”俱乐部的主席,这是一个天主教辩论俱乐部,旨在解决知识分子和科学领域中所存在的天主教的差异。基斯谈到他的基本自由原则时,说:“我们的思想应该保持无拘无束,宽容地体谅他人,而不要一味地沉迷于宗教事务,要清楚我们所期望的,并让人了解它。宽容是社会相处的第一准则。”[14]1904年,基斯成为奈美根天主教选举协会“为了所有人的权利”的地方议员,他令人吃惊地大刀阔斧地展开各种积极活动,以推动奈美根城市的发展。在他的改革之风的吹拂下,奈美根这个小城镇迅速发展起来。他撰写了一份关于地方发展形势的报告,并呼吁镇政务会更大力度地改善糟糕的民众的健康状况,解决住房建设与工业部门的债务问题。技术革新可以提高生活水平。基斯在奈美根组织了第一届电器博览会,主持了马斯河与瓦尔河(Maas-Waal)之间运河的开凿、工业区的建设以及横贯瓦尔河大桥的建造。他几十年来为奈美根的发展而奋斗,当他取得成功之后,他写道:“只有那些为无私的理想几十年坚持不懈地努力的先驱们,在实现了伟大的目标后,才能真正地感受到他们确实活在一些人的心中。”[15]基斯的座右铭是:“击打!不断地击打!”(frapper! frapper toujours!)。他努力在地方改革中发挥历史性作用。伊文思的祖父和父亲一生执着的开拓精神,他们在临终时被授予荷兰皇家勋章。伊文思于1989年也同样获此殊荣时,他说,这项荣誉着实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就授予,“因为那样你们就不必设法去找授奖人了。”(1946年,伊文思在荷属殖民地拍摄了《印度尼西亚在呼唤》后,遭荷兰政府驱逐流亡他国,后来长期定居法国,直到1989年6月28日辞世。这是伊文思讽刺荷兰政府长期对他的不公——译者注)
对于技术进步的信仰,对伟大目标的执着追求和留名青史的决心,这是伊文思的父亲教育理想的核心支柱,伊文思完全继承了父亲的这一理想和精神。这就是德国人所谓的“潜移默化”,从而形成了伊文思的事业之路。伊文思父亲的理想开始于当地的奈美根小城,而伊文思的理想则是在世界范围内以纪录电影来实现。纵览伊文思的全部作品,多少桥梁、高炉、大坝、工厂和发电站呈现在我们眼前?伊文思一生的作品似乎完美地诠释了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的,20世纪发生的最重要的革命是具有七、八千年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革命。这场革命远比“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暂时性冲突影响更为深远,而且这场革命与意识形态的差异无关,两个体系都在追求这场革命的实现。伊利亚·爱伦堡(Ilja Ehrenburg)1931年写道:人类战胜自然,这是伊文思电影的一个标志。无论是须德海围海造田勤劳的荷兰工人,还是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附近空旷平原上建造高炉的年轻工人,或是同心协力为农场供电而工作的俄亥俄州的农民,抑或是在泥泞的田地与耕牛一起劳作的中国和越南的农民。他们都是以自己的双手改变世界面貌的令人钦佩的人们,是伊文思影片中着意刻画的肖像。伊文思以饱含爱和尊重的影像展现了这些集体劳动者令人惊异的力量。安娜·萨格斯(Anna Sehgers)称之为“弱者的力量”。L.J.乔达安谈到伊文思1932年之前的影片时,指出:“伊文思这种对无产阶级的态度并非源于他的政治立场,而是由于一种本能的倾向,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与德国无产阶级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本能的倾向赋予伊文思作品一种显著的朴实、清晰和坦诚的品质。”[16]伊文思与无产阶级的“这种亲密关系”萌芽于童年在父亲的照相器材商店里。青年伊文思与那些技工、精密工程、光学和化学方面的技术人员不拘礼节,关系亲密。尽管伊文思的父亲被认为是个刚愎自用的人,但包括伊文思在内的员工们却形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伊文思在他的影片中反映了霍布斯鲍姆所谈到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这场革命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在影片《意大利不是穷国》(1960)中,与画面上西西里岛古典神庙相配的解说词是:“从古希腊库克罗普斯时代以来,这里几乎没有变化……直到石油的发现。”1939年上映的于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以及越南拍摄的影片中,伊文思反复把古老罗盘的画面、佛像以及寺庙与19世纪的进步观念联系在一起。相似地是,伊文思的父亲也从来不放弃任何一次能够促进他的家乡技术革新与丰富悠久的历史联系的机会,他的家乡是最古老的荷兰小镇,历史可以追溯到巴达维亚人和罗马人生活的时期。
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全世界范围内所有严酷革命都在实现不久后,接着伴随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更极端、更残忍的暴力。满怀憧憬与理想,伊文思试图在社会的变革中实现自己的转变,在他的转变过程中,人性战胜了资本。1921年,伊文思在鹿特丹商学院学习时,第一次阅读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作为学生会主席,他主张自由和包容,保护反对意见。当时,伊文思一定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势不可挡的进步思想,这种思想恰好与他父亲的实业天主教思想暗合,伊文思的父亲曾写道:“只有坚定的信念才能保证我们沿着曲折的道路不断地前进,实现我们最终的目标。”1925年,伊文思曾在一首诗中写道:“一起实现最终的目标”。伊文思在人生暮年谈及“风”的时候,再次使用了相似的表达,他认为风是“人类前进的巨大潮流,它不同于各种涓涓细流、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业已没落的文明。我仍然坚信,这股巨大的潮流能够推动我们向更好的方向前进”[17]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给荷兰带来了轻微震荡。1921年至1924年,伊文思在柏林学习,并在工厂进行实习训练,因此,他直面了战后柏林狂暴的政治骚乱的后果。当时,伊文思完全被新生事物所震惊,于是,他撰文抨击父辈一代所持的狭隘的道德观、价值观和物质主义:他写道:“坚持理想对人类来说是必要的,使理想高于社会的机械化对人类来说更是必要的。”[18]
20年代初期,伊文思先赴柏林,返回阿姆斯特丹,之后到巴黎,他结识了一群艺术家朋友,他们都一致反对资产阶级道德观,渴望改革。伊文思以一种虔诚的艺术之心和“宏大而热烈的生活”拥抱“生机论”(vitalism,一种关于生命本质的学说,它主张有某种特殊的非物质因素支配生物体的活动。——译者注),一种表现主义的变体与对战时“黄昏人”(Menschendämmerung)的浪漫回应体。当时,毋庸置疑的领军人物亨德里克·马斯曼(Hendrik Marsman),也是伊文思的诗人朋友。马斯曼曾写道:“艺术与生活是合二为一,不可分割和无从区别的。”此后,伊文思终生都坚守了马斯曼所说的这种社会参与的态度。这种忠诚只有在其诞生的时代语境中才能被准确地理解和阐释。这是在当时的各种先锋艺术领域中形成的一种共识,如对新造型主义(De Stijl)的认识,彼埃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写道:“凡在生活中是真实的,在艺术中也必然是真实的。”由于资产阶级不能够避免战争的发生,因而战后它在道德和政治上均告破产,从而艺术家被赋予了神职人员布道的职责。“艺术的象牙塔变成一座指引下一代寻找坐标的灯塔。”[19]当时,许多艺术家都自命不凡地视自己的工作如使徒般的神圣。
20年代,伊文思的一位无政府主义朋友亚瑟·穆勒·雷宁(Arthur Müller Lehning)也在宣扬艺术家的空想社会主义角色。雷宁毕生致力于出版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的著作,甚至有传言说,伊文思替雷宁投资出版巴枯宁的著作。伊文思和雷宁还一起策划出版一本国际杂志以便于先锋艺术家自由表达观点。雷宁确实主编出版了《i10》杂志(1927年1月至1929年6月),是一本“第十国际”的杂志,伊文思作为一位普通作者曾为该杂志撰稿,其他的撰稿人还有新造型主义先驱彼埃特·蒙德里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以及荷兰现代艺术家莫赫利-纳吉(Moholy-Nagy),在这些艺术家的共同努力,《i10》成为当时的一份权威刊物。
在亚瑟·雷宁家中,伊文思邂逅了德国摄影师杰曼·克鲁尔(Germaine Krull),他们一见钟情并于1927年结婚,克鲁尔有着令人吃惊的丰富个人经历。当她还是一名年轻学生的时候,她就支持社会主义政治家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在慕尼黑推行的苏维埃共和国体制,并拍摄了他被暗杀后的照片。她年纪很轻就两次堕胎,曾追随左翼革命者经瑞士流亡到澳大利亚,被捕后辗转至莫斯科;随后.她在第三次国际工人运动中被捕逃回柏林,此时,她的共产主义理想已经彻底幻灭了。谈到伊文思对她的吸引时,她写道:“他的目光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观察事物的方式……我觉得自己莫名其妙地被他吸引了。他看待事物的朴素方式给了我信心,因为一切在他看来,都是那么的简单和纯洁。”[20]她与伊文思的婚姻是建立在平等和独立的基础上的,这也是她一生中维持得最长的一段关系。伊文思是第一个给她介绍资产阶级实业家领域的人。伊文思与克鲁尔一起居住在阿姆斯特丹期间,他们结识了一些艺术家朋友,尽管这个圈子里的朋友政治分歧很大,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个人交往与合作。这些人中诸如扬·托洛普(Jan Toorop)、埃里克·维希曼(Erich Wichman)、派克·考赫(Pyke Koch)、J.C.布拉姆(Blom)转向右派政治立场,信奉天主教、墨索里尼、民族主义、贵族秩序和法西斯主义;而其他诸如查理·托洛普(Charley Toorop)、亨利·匹克(Henri Pieck)、皮埃特·兹沃特(Piet Zwart)、保罗·舒伊特玛(Paul Schuitema)和伊文思则深受俄国实验派吸引,倾向于左翼政治观点。当时大家保持着友好的联系,政治观点的抵牾不是很尖锐激烈,这种状况到1929年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9年以来发生的经济危机和对法西斯主义必须做出支持或反对的选择,使艺术创作队伍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回顾这段历史,伊文思说:“那个时候,我并不为政治感到困扰,以至于我认为我的艺术是非政治的。但在当时,我却以这种非政治的影片支持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的。”[21]
艺术先锋
尽管伊文思的父亲基斯·伊文思是个地地道道的商人,但他却对艺术充满非常浓厚的兴趣,家中时常有艺术家出入,画家兼平面设计艺术家尤金·鲁克(Eugène Lücker)是伊文思家中常客,而尤里斯嗅到一种先锋艺术气息,是在1917年奈美根举办的亨利·皮埃克的作品展上,一张海报上画着他像是为了什么东西着魔一样在攻击着亚麻布。这次展览还引发了一个丑闻,在一个独立展室中,挂帘的后面有5个裸体像。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基斯·伊文思邀请画家为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画一幅三联画(在这幅三联画中,可以看到背景花园里的伊文思)。那些年,亨利·皮埃克常常为卡皮照相馆制作广告宣传品。皮埃克作为一个插图画家应邀访问了匈牙利的苏式共和国之后,他被共产主义深深吸引了。在20年代末,亨利·皮埃克与尤里斯·伊文思的关系越发密切,二人一起在阿姆斯特丹的左翼文化圈里工作,皮埃克曾为爱森斯坦以及其他共产党的电影制作海报。
基斯·伊文思与各种艺术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11年,他在奈美根组织了当时被认为是现代天主教艺术的杰出人物扬·托洛普的第一次展览。1916年,基斯·伊文思雇佣了一些著名的荷兰艺术家理查德·罗兰·霍尔斯特(Richard Roland Holst)、约瑟夫·门德斯·达·科斯塔(Joseph Mendes da Costa)以及莱昂·卡奇(Lion Cachet)来设计和装饰他在阿姆斯特丹的卡皮照相馆。当时这几位艺术家已经功成名就了,但是他们的“新艺术”(Jugendstil)很快就过时了。
尤里斯·伊文思在柏林接触到一些新的艺术潮流。在柏林,他表现出对艺术的兴趣:搜集大量的艺术书籍并复制一些表现主义艺术家,如弗朗茨·马尔克(Franz Marc)、乔治·格罗兹(Georg Grosz)以及梵高等人的艺术作品。作为一个电影人,他后来经常利用这些艺术书籍作为研究资料。他还与艺术家朋友们经常光顾剧院和电影院,然后在浪漫的咖啡馆终结夜晚。“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结识新人和艺术家,并融入到他们全新的激情中,因为他们与追求物欲和腐败无关……并支持任何与此相关的事情,这些对我战胜腐朽的旧思想和观点非常有益。”[22]作为艺术吁请的回应,伊文思与表现主义诗人亨德里克·马斯曼一起去观看罗伯特·威恩(Robert Wiene)、S.T.杜邦(S. T. Dupont)以及其他艺术家摄制的表现主义电影。影片《杂耍场》(Variété,1925)是一部主观视角的电影,该片激发马斯曼创作了一首充满狂喜的诗:“我自己做到了,从一个高空秋千飞跃到另一个高空秋千,并在空中令人眩晕地翻了跟头,在那永恒的瞬间,哪里闪过一道亮光,在我的身下?在我的头顶?在我的某一侧还是在整个宇宙?这道光甚至比去年的流星雨还要亮……”[23]马斯曼将这首诗送给当时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去黑暗的放映室观看影片的尤里斯·伊文思。正是杰曼·克鲁尔引领伊文思进一步深入到艺术、政治以及生活中去。最初,她拍摄一些类似符号化的“舞台摄影”(tableaux vivants),但在使用了伊卡莱特(Ikarette)照相机后,她的照片获得一种无艺术技巧的快照特征。伊卡莱特相机便于操作,所拍摄的照片风格与基那莫(Kinamo)相机特点相反。这时她拍摄的照片有时脱焦,没有美感,也没有提供任何信息,她的摄影主题与当时其他的女摄影师所表达的主题完全不同。1925年,伊文思和克鲁尔在阿姆斯特丹安家后,克鲁尔经常去港口观景。港口巨大的金属结构的起重机令她内心充满了恐惧,她悲惨的早年生活经历导致死亡的恐惧始终萦绕着她。而要战胜这种恐惧,她只有通过手中的相机来控制起重机。通过俯视的角度,对角线构图,以各种金属结构为拍摄主体,由此,克鲁尔的作品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客观性,她凭此作品成为当时新派摄影风格的领袖。她说:“要以一种未经打磨的、中立的、不带任何偏见的目光去观察事物。”她的朋友瓦尔特·本雅明对她的作品这样评论道:“当摄影与它自身分离以后,就像桑德(August Sander)、杰曼·克鲁尔、布拉斯菲尔德(Karl Blossfeldt)所做的那样,它才成为一种创造。”[24]克鲁尔不带任何偏见,不受教条和错误观念的约束,她拍摄了那些流浪汉、酒吧里的醉鬼、集市、政治领袖、风景、裸体以及肖像等。除了裸体之外,克鲁尔广泛的室内外拍摄对象的选择特点,我们在伊文思早期的电影中同样也发现了。1927年初,伊文思依然在放荡不羁的艺术追求生活与家族企业副总裁兼继承人的职位之间犹豫不决。他没有勇气直面这种冲突并进行斗争,因此,他也不可能摆脱父亲对他的压力。伊文思在等待着一个机遇,以唤醒他当时尚在沉睡着的艺术抱负。
电影联盟和第一个电影年
1927年5月13日至14日的夜晚,是伊文思期待已久的一个历史性时刻。门诺·特·布兰克(Menno ter Braak)、亨里克·肖尔特(Henrik Scholte)、迪克·本尼狄凯(Dick Binnendikj),这几个阿姆斯特丹的大学生决定成立一个联盟,可以放映一些先锋派电影。伊文思的弟弟汉斯把伊文思介绍给这个联盟,以期放映当时属于禁片的苏联导演弗谢沃洛德·普多夫金(Vsevold Pudovkin)的影片《母亲》(1925)。伊文思的以他精湛的技术知识和卡皮公司的设备,将普多夫金的这部煽动性的影片为充满激情的观众放映了两次。影片是在亨里克·肖尔特(Henrik Scholte)宣布电影联盟即将成立之际放映的。两天以后,肖尔特起草了著名的电影联盟宣言:“它是关于电影的联盟。我们每看一百次电影,只有一次看了电影,其他的我们看到了电影业。大众、商业体制、美国电影这些都是迎合低级趣味的东西。在这个阶段中,电影和电影业是互为天敌的两个方面。我相信纯粹的、自发的电影。如果在我们的手中不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电影作为艺术和未来都是没有希望的。”
严格意义上说,上述宣言中最后一点是伊文思的贡献。次日,也就是1927年的5月16日,亨里克·肖尔特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更大的艺术兴趣是,尤里斯·伊文思计划根据亨德里克·马斯曼的剧本拍摄一部影片……这将会是第一部真正的荷兰电影实验之作吗?”伊文思让当时肖尔特的现任女友,演员夏洛特·凯伊勒(Charlotte Köhler)试过几次镜[25]。然而,这个拍摄计划仅停留在愿望上而没有多少进展,问题出在伊文思所选的马斯曼的剧本上。1927年出版的马斯曼所创作的散文诗《飞翔的荷兰人》中,并没有一位女主角,但这也许正好提供了一个拍摄美丽佳人的理由。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伊文思好像使用了几位散文作家和艺术家朋友们的剧本。杰夫·拉斯特(Jef Last)在剧本《死街》(Die Strasze)的空白处批注:“部分已经由伊文思拍成电影”[26]。我们还发现在埃里克·维希曼(一位无政府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放荡不羁的艺术家,总是在一次骚动之后预见新的潮流)的一部名为《病镇》(Sick Town , 1927)的剧本中,尤里斯·伊文思起了主导作用。就像伊文思的早期影片一样,这部超现实主义的剧本将故事设定于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咖啡屋中。电影联盟成立以后,这个剧本已经拍摄完成的一些镜头曾经给观众放映过。剧本凸现了非凡的自动摄影机的工作及构成画面的节奏:一只手摇动着摄影机上的轮子,跨越摄影师伊文思的手。接着维希曼和伊文思两人互相对拍……一个脚本开场是“天空中的序曲”,“灰色如铅的天空。暴风骤雨。地上一片泥泞,大雨滂沱。一条雨巷。人们穿着雨衣,竖起领子,行色匆匆”。甚至一位荷兰艺术家的动画作品也被拍摄下来。伊文思摄制该片的初衷并没有限定为纪录片,而是想拍成故事片。最重要的是,他是希望同时更新虚构片和非虚构片电影语言的先锋派电影人。
电影联盟的第一年,即1927年5月16日到1928年5月5日《桥》的首映之间,几乎没有资料和影片留下来。即便是伊文思最亲密的朋友,对他这一年的情况也知之甚少。在这一年里,伊文思似乎把时间都用在了培养自己上了,他关注电影的每一个方面。他狂热地在“黑暗中”与“无声中”工作着,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他都沉湎其中。作为电影联盟的技术顾问,他有机会观看和分析各种影片。就这样,想必有200公里的胶片在卡皮的电影放映机上转动过。伊文思通过“拼写”这些影片,从中学会了电影的语法、规则及本质。在电影联盟的第一期杂志中,伊文思用了与莫赫利-纳吉同样的话来描述电影科技的本质:“连续画面在时间上的持续;一个画面的运动方向和速度与下一个画面的相互对比;前一个画面构图的黑白分割与下一个画面的黑白分割相比较。”电影在视觉与心理上的规律、类似于数学的定律,尤其是在纯电影对伊文思的吸引力更大,但“摄制一部影片不是一个求和的计算过程。那它是什么呢?”他思考着,试图在具体的实践中找到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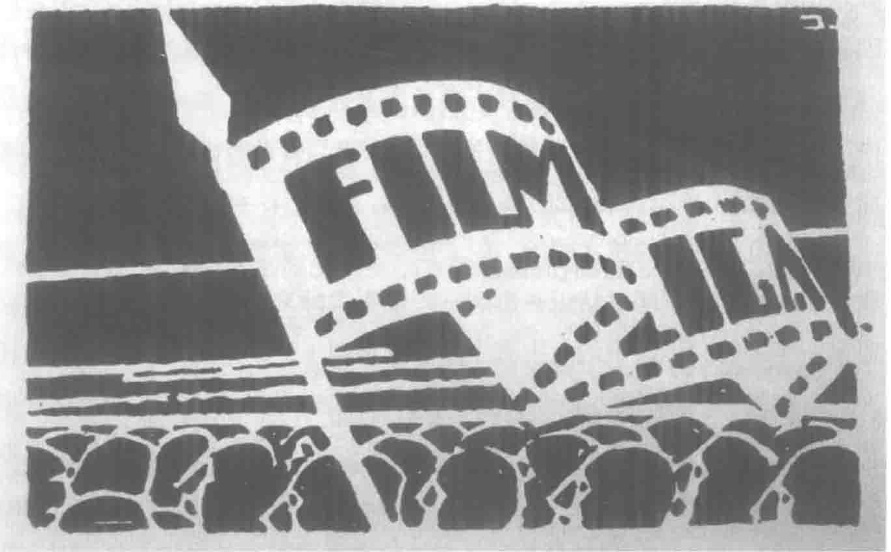
L.J.乔达安为电影联盟第一期杂志画的插图
伊文思与杰曼·克鲁尔从位于阿姆斯特丹的达姆拉克(Damrak)的家进城,要经过一家证券交易所。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因为早在1927年4月他们结婚同居的时候,克鲁尔认为她必须要有荷兰的护照,同时还要有巴黎的居住证,但这紧张的关系并没有妨得两人从巴黎到阿姆斯特丹访问途中的亲密合作。他们经常经过达姆拉克到海堤(Zeedijk)和奥德·兹德斯沃博沃(Oude zijdsvoorburgwal)地区。克鲁尔拍摄了一些仓库和港口的照片,伊文思拍摄了波光粼粼的水面,水边晃来晃去的腿,正在建造的一条街以及一个泵站,他称之为《电影写生》(Kinosketchbook,1927)。海耶斯大妈公寓中的一个咖啡馆成了新电影试验的汇聚场所。每天进出咖啡馆的人深深吸了画家查理·托洛普,她在这里画过两幅油画,杰曼·克鲁尔拍摄过同样的人,当然,这些人同样吸引了伊文思。查理·托洛普的油画《旅馆》体现了电影剪辑技术对她的影响。她所画人物的头部与身体并不相关,三维效果及比例也并不遵从焦点透视法则。她经常试图在作品中运用剪辑的特征。伊文思将他自发拍摄的、未经剪辑的一系列镜头称为《海堤电影练习》(1927),是他的第一部作品。
作为电影联盟的技术顾问,伊文思经常出国观摩影片,寻求适合电影联盟放映的电影,同时结识并邀请一些电影大师来阿姆斯特丹。在电影联盟第一年,伊文思结识的人中有:弗谢沃洛德·普多夫金、吉加·维尔托夫、谢尔盖·爱森斯坦、杰曼·杜拉克(Germaine Dulac)以及阿尔伯特·卡瓦康蒂(Alberto Cavalvanti)。1927年10月中旬,伊文思在柏林和德累斯顿分别拜访了汉斯·里希特(Hans Richter)和沃尔特·鲁特曼(Walter Ruttmann)。沃尔特·鲁特曼的工作室给伊文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鲁特曼的抽象电影,如《作品2号》(Opus II)、《作品3号》(Opus III)以及《作品4号》(Opus IV),看起来只是简单技术运用的成果,一些简单的比例模型、一部老的摄影机和一点技术足矣。我也可以这样做,伊文思一定这样想过。鲁特曼的电影《柏林,大都市交响曲》(1927年)对伊文思的影响非常大,因为,这是第一次将纯电影(cinéma pur)的规则与城市纪录片相结合;这二者的结合产生了一个的戏剧性的统一体,但却没有故事片那样的情感内涵。
回到荷兰后,伊文思在他的信箱中发现马努斯·弗兰肯(Mannus Franken)寄来的关于雨的电影剧本。一个星期以后,伊文思回信说:“雨的剧本,我正在这里漫步雨中,到处看看。这几天我将会拍一些。”几个月后,伊文思给几个朋友放映了他拍摄的东西,但是影片的主题看起来太诗意,自然看起来过于变幻莫测了,因此,对艺术家来说很难驾驭。而且,伊文思注意到,对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来说,确实面临一个困境,每一个瞬间都不会重演。真正的艺术就是在令人信服的现实中,捕捉到最富有感染力的时刻。而如果重新表演,效果就不同了。虽然伊文思很快找到了一个主题,以一种新的、客观的方式来表达城市生活,但他大约用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影片《雨》(Rain,1929),报纸称该片为“心绪电影”。伊文思在积极地寻求更简单的主题。最初,他在去巴黎见杰曼·克鲁尔的途中发现了它,于是他拍摄了一部关于喧嚣的城市交通运动的影片。克鲁尔的摄影作品与伊文思的影片相呼应:从克鲁尔寓所拍摄的巴黎屋顶的画面,歌剧院、黑色廉价的出租车以及布加迪车等。影片《对运动的研究》(Etudes de mouvements,1928)中,摄影机跟着一辆车从左向右运动,经过了杜伊勒里宫,一直跟到另一辆车从另一个方向朝镜头开过来,镜头又从相反的方向跟着它。摄影机就是这样游荡着,成为一次对运动的研究。
1927年12月,伊文思和汉斯·范·密尔顿(Hans van Meerten)研究摄制一部《我—电影》(I-Film,1928)的可能性,影片中他们努力调动观众的眼睛,不仅是从座位上静止地观看影片,而且要让观众参与到影片的活动中去。在咖啡馆里,摄影机观察一杯啤酒,当啤酒渐尽,整个咖啡厅纳入杯中。令人惊奇的是,伊文思精心设计了让摄影机模仿人眼的运动。摄影机架在一个四轮小车上,三脚架上的摄影机模仿着人眼的转动,俯视和仰望。然而,这个主观的摄影机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当伊文思观看这些镜头时,它们显示两种可能性:“一个是我醉醺醺酿地走在卡弗斯达特街上;或者:卡弗斯达特看起来快要被淹没了,我要划船去大坝上。”[27]这两个实验表明,伊文思正利用主观的摄影机工作,寻找一种新的方法来证实感觉的真实性。
《桥》
在进行了实验、试镜头以及初次尝试拍摄《雨》之后.伊文思开始寻找一个较大的题材以实践他新获得的知识,铁路建筑师斯堡·范·瑞沃斯崔(Sybold van Raverstryn)就像电影联盟的其他几位积极分子,如:建筑师里特维尔德(Rierveld)、贝尔拉格(Berlage)、欧德(J.J. Oud)和范·伊斯特恩(Van Eesteren)一样,建议伊文思拍摄鹿特丹的一座名为“电梯”(De Hef)的铁路桥。这座钢铁庞然大物是1927年10月投入使用的,是一个科技的奇迹,即机械的运动以及横向纵向的线条非常理想地与伊文思所认为的电影本质相合:有节奏和方向的运动。
这个题材的选择也受到了他父亲1927年经议会委任修建位于奈美根的交通桥的启发。数十年来,基斯·伊文思都热衷于与工程师讨论最新的科技发展。最终,它变成了一座巨大的钢铁弓形桥,正如他父亲骄傲地宣称,当时是欧洲最大跨度的桥。所以,这个题材对伊文思的父亲来说非常行之有效,可以说服他的父亲允许伊文思在工作时间去拍摄这部影片。
当伊文思1928年开始拍摄时,他没有身为艺术家和电影人的感觉。这一点在影片《桥》完成前后的题为“业余电影及其可能性”的系列讲座中表达得非常清楚。讲座中,他描绘了一幅关于电影媒介起源的图景,他阐释说:“电影最早是令人好奇的杂耍,然后依附于集市。”他认为业余电影将会丰富专业电影,就像业余摄影已经对专业电影所做的贡献一样。他的父亲一年前在一篇关于摄影史的文章中,表达了以上观点:“业余摄影师在选择拍摄对象时更为自由,同时也不受大众庸俗趣味的干扰。摄影师阿杰特(Atget,法国摄影师,以巴黎街头照片而闻名——译者注)1900年前后就可以在巴黎拍摄空无一人的街景。摄影最初一味地模仿绘画艺术而没有考虑它自身技术的可能性和规则,但到后来,它终于走出了只起装饰作用的阶段而具有了历史文献的价值,这得感谢业余摄影的贡献。”[28]尤里斯·伊文思与电影起源画了一条平行线,它起初是模仿戏剧。而业余电影则改变了这一点:“就像绘画、摄影以及音乐一样,电影遵循自身的规律,以活动的影像来制作艺术品的可能性,在经过了很多年的‘复制阶段’以后,现在终于实现了。人们经过很长时间对电影的‘阅读’之后,现在开始学习如何‘拼写’了。”

20年代末,电影联盟成立后,伊文思邀请爱森斯坦访问阿姆斯特丹
伊文思认为业余电影是将电影艺术提升到一个更高水平的关键,这种对业余方法的强调来自于他所使用的基那莫摄影机,通常专业电影导演基本上不使用这种摄影机。伊文思在德国职业学院训练时,就非常熟悉这种摄影机,手里拿着它,他成为“摆脱肩扛”工作的先驱。杰曼·克鲁尔在鹿特丹拍摄大桥的照片时,也使用了一种非学院的方法,即使用一种便携式的照相机——伊卡莱特相机进行拍摄。她对拍摄对象的选择也启发了伊文思,因为在此之前,她在阿姆斯特丹以及其他港口已经拍摄了一些钢铁结构的照片。在巴黎,克鲁尔与画过一系列埃菲尔铁塔的罗伯特·德芳内(Robert Delaunay)成为好友,在她出版的成功的影集《金属》(Metal,1927)中,埃菲尔铁塔也成为她的一些照片的模特。伊文思发现电影的本质是因为他使用的这种摄影机只有一个镜头,画质较为粗糙,没有三脚架,无需借助于窍门和装置或者被导演分心。“没有人记住第七艺术的规则。但我们必须发现这些规则。电影人一定要认识到运动是它的主导因素。只有沿着这条道路电影才能回归它的本质。每一种艺术形式的规则都是基于它的特征和所依存的材质和技术的需求。”电影联盟中最重要的艺术理论家门诺·特·布兰克也支持伊文思的这个观点。在他撰写的关于电影美学的文章中论述道:“电影作品的统一体是视觉节奏的统一体;换句话说,电影外在的节奏必须作为内在节奏的象征,一个激动人心的连贯体。在组织过程中任何一个错误都会损伤戏剧性的发展;每一个画面不仅是与技术有关,而且与它上一个和下一个画面具有一定的心理联系。”[29]尤里斯·伊文思在剪辑《桥》的时候,准确地说,就是在努力探索这种感知心理。伊文思得益于与心理学家的谈话以及卡片组织结构影片的方法,所以,他没有忽视内在的联系。
不同于克鲁尔在桥上以对角线构图拍摄的那些照片,伊文思把自己限定在垂直和水平的方向上。与彼埃特·蒙德里安在作品中也努力保持相反的运动和相反方向的对应物之间的平衡不同。首先,伊文思想通过拒绝为影片命名来加强影片的抽象的冲击力,并以白底上闪烁的黑色方块最后一个镜头表明了伊文思希望该片接近埃格林和鲁特曼的“绝对电影”。伊文思对抽象艺术非常感兴趣,因为就在拍摄《桥》的这一年,他设计了以锥体和棱镜投射光而形成一个完全抽象和先锋的舞台背景。伊文思这样有强烈意指的光效设计,可以与当时莫赫利-纳吉的空间灯光调节(Licht-Raum Modulator)相媲美。在拍摄《桥》的同时,伊文思还给莱顿大学拍摄科教片,他使用微型摄影机拍摄,获得了一种抽象的形式世界。
在拍摄和剪辑《桥》的过程中,伊文思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所做的是非常特别的。以致他失去了业余电影人的特征:“在剪辑的每一刻,我都发现自己在创造一种张力,以至于我甚至不敢下手去剪辑这部影片。每天晚上,我都怀着一个刚刚发现处女地的先驱的热忱和激情工作着。”[30]
伊文思是作为一个业余电影人开始拍摄《桥》的,而在1928年5月5日的影片首映的那个夜晚,在鲜花和掌声之后,他已经被视为一位电影先驱和荷兰电影的翘楚人物。“《桥》摄制于一场旨在对抗那些大规模商业制作的不亚于谋杀的无聊电影的运动中。它成为战斗的号角和信条。而且,该片的拍摄完全是他自己的一次冒险行动,而没有受任何委托之累。换句话说,影片的拍摄虽然备受经费限制,但同时却获得了彻底的艺术自由。”[31]这是伊文思最具有美学和形式感的一部作品,影片中几乎看不到人,没有心理活动,也没有解说词,因此,该片被电影联盟奉为圭臬。而在伊文思开始表达政治立场时,人们对该片的赞赏也大大降低。
伴随着影片《桥》的上映,伊文思结束了一年的创作实践,尽管影片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伊文思还是不能告别卡皮照相馆。“卡皮照相馆对我的牵制实在是太可怕了。我所喜爱和感兴趣的领域就在我的眼前,而我却无法企及。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了!”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尽量将卡皮的生意按照他的愿意方向发展,并学会利用卡皮的资源与他的爱好相结合。
他欣赏那些国外的独立先锋电影人以及他们不受商业委托的限制。在最初的几年里,伊文思能够开创他的独立电影事业得益于卡皮照相馆提供的便利条件。他利用卡皮的摄影机、放映机、放映室以及人员——发行、联络以及翻译等。渐渐地,他与卡皮成为一种合作关系。在这种合作方式下,伊文思的私人秘书海伦·范·东根(Helen van Dongen)成为一名天才的剪辑师,努力使其成为一项优秀的事业。她对伊文思的多部优秀影片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后还帮助弗拉哈迪剪辑了影片《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1948)。约普·赫伊斯肯(Joop Huisken)则成为东德电影最初10年纪录电影的奠基人之一。在尤里斯·伊文思的哥哥威姆的建议下,父亲在卡皮内部建立一个电影组织(Film Organisation),但父亲对儿子弃家族事业于不顾感到伤心。据伊文思的父亲说,伊文思为了自己的电影项目从卡皮挖走了近100万荷兰盾(按现在的标准算)。据伊文思日记称,父亲基斯称他为背叛者,并指责是他导致了卡皮在30年代的破产。伊文思对此事深感愧疚,因此,在几十年后的60年代再次使用他的父亲最初使用的“卡皮”这个名字,作为他和玛瑟琳·罗丽丹的制片公司的名称。伊文思以这种方式使他成为家族企业的名符其实的继承者,只不过形式不同罢了。
蓄势待发
在伊文思的先锋作品得到认可的最初几年里,他首先是在实践上进行自我教育。他像疯子一样地工作着,为他将来的作品打下坚实的基础。后来,伊文思把纪录片描述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即一种能跨越剧情片和新闻片之间鸿沟的一个全新的领域。依据伊文思自己的界定,可以清楚地看到:伊文思的影片不能被简单地认定为纪录片类型。即使在他创作初期,他已经开始使用拍摄电影的各种方式和手法,包括剧情片和新闻片的创作手法。在1927年至1931年的4年中,他所摄制的作品类型包括:科教电影(大学使用的显微电影)、家庭电影(《T Zonhuis》和《希亚的成年礼》)、剧情片(试拍《飞翔的荷兰人》、《街道》、《病镇》、《打桩》、《Donogoo Tonka》,其中几部有些超现实主义风格)、新闻电影(《VVVC-Journals》)、社会报道电影(《贫穷的德伦特》);商业电影(《飞利浦收音机》、《杂酚油》);以及许多其他的委托电影(《我们在建设》和《须德海》),甚至还有动画电影(《病镇》)、美学形式和运动研究(《对运动的研究》、《桥》);诗意的自然记录(《雨》、《打桩》)、主观电影(《我—电影》)、政论电影(《破坏与建设》)、电影写生(Kino Sketchbook)、抽象艺术(灯光与舞台设计,包括《桥》的最后一个镜头,《飞利浦收音机》的最后一个镜头,以及许多早期影片的特写镜头)。他也可以运用完全不同的手法:既可以用微距镜头,也可以从飞机上航拍全景镜头;表现主义影响源于生机论与抽象的绝对电影;剧情片和新闻片;既接受工会或共产党组织的委托,同样也接受资本主义大企业的任务;既使用主观的意象,又使用科学的描述;既追求形式美学,又进行社会报道;动画与新闻画面并用等等。似乎罕有人像他这样,一开始就具有如此多方面的才能和灵感并引以为荣。实际上,在他后来作品中的所有元素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来了。正如伊文思自己谈到这一点时说:“在某种程度上,我非常高兴我能够有机会在开始另一项更加重要的工作之前,已经奠定了扎实的技术基础和优秀的创造能力。”[32]
那些仅仅视伊文思为《桥》和《雨》这些早期影片的导演的人,一定忽视了他的许多试拍和失佚的影片,因此可能导致忽略这样的事实:即他后来影片中的所有要素,已经在早期的作品中尝试过了。他继续努力和尝试拍摄剧情片,以政治立场或者更诗意的电影来替换反美学电影。用这样的方法,他的各种电影技巧得以发展,他的影片定义为自然、劳动、政治和文化的主题,呈现一种良性循环的态势。
所有早期作品里,或多或少形成对比的,伊文思早期电影中的所有元素在影片《英雄之歌》中第一次被结合起来。在《英雄之歌》中,新闻影像,兼容剧情片、自然风光片以及社会报道、动画片的各种元素进行重组,并组织个人与集体搬演一些场景,镜头上既有飞机上的航拍全景镜头,也有近距离的特写镜头。尽管因为莫斯科的几个委托人的干扰,使《英雄之歌》未能非常令人满意地将各种元素融汇在一起,但影片所使用的方法为他的作品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比在影片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乡村里传统的农场劳动与马格尼托哥斯克的工业劳动之间的对比;苏联的工作与西方失业的景象对比;年轻一代与老一代的对比;个人与集体的对比等等。伊文思不用演员,而是让工人自己来扮演主要的角色。他写道:“在《英雄之歌》中,我将使用的方法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通过我在以前各种方法中积累的经验及与当地共青团员亲密的个人接触中发展形成的。”[33]这种辩证法与爱森斯坦的电影理论有关,并与同时期的布莱希特和艾斯勒的作品在意义上颇有相似之处。
先锋派和幻想
1927年,伊文思抱着很高的期望加入先锋派。据伊文思的观点,纪录电影不能通过与剧情片针锋相对来获取自己的位置。1927年,电影联盟的支持者们认为电影制作是“大量化、商业化的、美国式的、媚俗的”,并且把电影和电影艺术当作互相的天敌。伊文思总结道:“电影产业通常以糟糕的影片来表达它自己,以迎合大众低级趣味的影片来取悦观众。”[34]为了回归其本质,要以摄影机和电影为先,而不是一味追求真实或者表演的自然——电影会成为一种繁荣的艺术形式。“不是内在的一系列思想,但客体本身要求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序展开。”[35]在“没有错误的幻想”的原则引导下,伊文思满怀着对电影的真诚,他认为这是唯一的以革命的方式来改变电影语言的道路。“在当今的情势下,纪录电影无疑是接近真实电影的最好方式。你无需担心迫不得已去剧院或音乐厅,简言之,去那些不存在电影的地方”;而且“纪录电影是留给先锋派电影人唯一的对抗电影产业的手段”。[36]伊文思写道,“先锋电影是抗争电影产业中出现的艺术通货紧缩的‘突击队’”。对伊文思来说,纪录片作为艺术已经是一个规范的概念了。“一名纪录电影工作者不能撒谎,不能违背真实。事实不容背叛:纪录电影要求电影工作者的人格,提升为艺术家的人格,以此来摆脱追求庸俗的时事性,摆脱简单的摄影术”[37]。这种强烈的道德观始终成为伊文思作品的一部分:保持一个人的独立性、远离商业和幻想,让纪录电影的影像比故事片更“真实”和更“准确”。
后来,伊文思总结,故事片与纪录电影之间其实并没有多少对立,而且在一些方面,二者都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与影响。事实上,拍摄故事片的念头始终萦绕于他一生,在他的各种影片中,都不同程度上具有虚构的元素。在《风的故事》中,伊文思和玛瑟琳·罗丽丹创新地实现了虚构与非虚构的结合。许多自诩为“运动派”的纪录片工作者,甚至激进的运动派,对纪录片的标准抱有幻想。直到1974年,巴兹尔·赖特(Basil Wright)写道:“某种意义上,纪录片是在本质上与民主相关的。它意味着具有反对和批评的权利。因此,在极权主义氛围中它不会繁荣。”[38]伊文思的作品对此观点是既赞成又反对。伊文思之后的两位荷兰纪录片导演阐述了他们对于纪录片标准元素的观点,扬·沃瑞曼(Jan Vrijman)曾谈到与伊文思的关系:“一个艺术家必须撒谎,一定不能说出真相。”约翰·范·德·库肯(Johan van der Keuken)强调说,电影人拥有的唯一的民主是摄像的民主:“影片中的民主是艺术家能够实现的具体的民主,因为他拥有影片最终的话语权。形式的民主和物质的民主,而且是虚构的,最终必定以某种象征的东西保存下来,因为现实世界中,它没有任何实际的力量。在伊文思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绝不接受这种无能为力。有人也许认为,他被迫冒着形式民主的风险(有时甚至放弃)去在现实世界中选择权力。”[39]最令人震惊的,是他在《激流之歌》(Song of the Rivers)中无耻的放弃。
电影联盟在30年代初期,也就是它创立后不久就解散了。那些开创这一运动的学生找到了工作,因此对活动失去了兴趣。电影院也放映其他先锋派的电影,随着有声电影的出现以及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人们的目光从形式主义转移到表达现实上,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也迫使艺术家们做出政治选择。30年代初期,就在先锋派认为他们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接受了电影院与电影工业的批评时,而伊文思却扩大了他的批评。这是他事业中断的一个信号。他两次赴苏联旅行,会见了爱森斯坦、维尔多夫、普多夫金之后,他的形式主义的批评被赋予政治影响力:“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是统治阶级麻痹大众阶级斗争的企图,并以虚伪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诱惑大众……”[40]这种政治先锋和艺术先锋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团结起来。人们相信纪录片是一种更适合于与社会主义观念保持一致的电影类型,即认为:社会主义是更好的社会制度,艺术家必须要认识到一种先知的社会角色,并且开始进行社会改革。“纪录片不仅必须要以情感为主旨、追求令人心醉的美,而且也应该唤醒沉睡的活力、激励改革。”伊文思对自己早年作为一名纪录片创作者的经历批判道:“我想象着自己以艺术形式上的革命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作战,但因为我的政治态度一切都陷人狭隘之中。”一件艺术作品可以通过“转换”来获得革命的内容。“转换”、“重新定义职责”、“重塑”等词汇经常让人想到伊文思、艾斯勒、布莱希特。他们的发展呈现出令人吃惊的雷同。他们三人不仅都出生于1898年的中产阶级家庭,在柏林革命与反革命风行之际,他们都居住于此。他们艺术与政治的成长也都非常相似:他们开始都是形式主义先锋派,而当他们参加了工人运动后,都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布莱希特说:“辩证的戏剧方法主要始于形式实验的符号中,并不涉及内容。它与心理无关,也与个人无关……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中产阶级的语境中,由内容决定的。”[41]这段话与伊文思的自我批评如出一辙。理论上,伊文思、艾斯勒、布莱希特三人的观点非常相似,如同本雅明的两篇非常著名的文章《作为生产者的作家》(1934年)、《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6年)中的观点,他以这三位艺术家为例,来回应卢卡奇(Lukacs)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现实主义概念)以及列宁的反映论。
伊文思的政治选择同样不可能离开他父亲和照相馆的启发。他从未学会为个人冲突进行斗争,因此,他只能通过与一种意识形态结盟,然后自己去远游来摆脱父亲对他的控制,他先是去了苏联,之后去了美国。尽管如此,伊文思还向父亲承诺他会回来振兴家族事业,在他们家族的年度报告中,伊文思依然名列副总裁之位。他无力解决与家庭的冲突,他明显地以银幕上的暴力冲突来弥补内心的压抑,伊文思在此与资产阶级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法国历史学者弗朗索瓦,孚雷(François Furet)称其为反对资本主义中产阶级的“自我厌恶”,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极权主义的诱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伊文思选择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是由他所接受的教育决定的。共产主义的信条认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模式沿着科学的道路向前发展,而每个人都会在共产主义前进的道路上发挥着独一无二的历史性作用。生活充实、富于冒险、前卫、追求理想、积极倡导并投身于新技术的变革,为人民谋福利并名垂青史,这些基本要素都是伊文思在他的家庭生活和先锋派运动中对自己所起作用的认识。作为“法国大革命”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对熟悉的自由主义来说,似乎是个遥不可及的更高层次的民主,因为它以人类平等、解放、进步为基础,包含工人阶级的利益。
伊文思在与故事片“不真实的幻想”所进行根本的斗争中,自己也隐藏了一些固执的幻想:纪录片是电影中高级的形式;共产主义是一种更高级的社会体制,艺术家是更有远见的人。他几乎穷尽一生才逐渐打破这些幻想。当他年近九旬的时候,终于实现了这个突破,这需要感谢玛瑟琳·罗丽丹与以及(《愚公移山》之后——译者注)一段漫长的治疗的抑郁,他勇敢的揭露,导致一部杰作诞生,其中想象、宗教和神话再次发挥了效力。伊文思重返他父亲的“信仰与科学”的信条,拥抱形而上学,与此同时,他得出的结论是:共产主义与他此前所认识的相比,更是一种“信仰”。他受乔治·梅里爱的启发,使他步入一个纪录片与故事片之间前无古人的中间地带——这是伊文思再次拥抱先锋派电影的一个创新,并为21世纪勾勒出雏形。这是伊文思在先锋艺术创作上的一个轮回,尽管伊文思自己更喜欢将其视为螺旋。“我认为这是个螺旋式的上升。它(《风的故事》)不是一个回归,而是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现在我能够拍摄这部影片,因为我经历了其他的各种历练”。他再次成为一个不拘一格的艺术家,一如从前,

《风的故事》结尾处的场景,伊文思开心地笑了
他厌恶享乐主义和消费社会,就像在摄影棚里所拍摄的那个场景一样,以一种略带批评的方式拍摄了在各种消费品包围中的新婚夫妇。影片中的生态学意识也发出声音,淹毁森林、水库、高炉、高压电线以及工厂等,这些他曾在影片中作为进步象征的事物,现在却成为破坏的例证。而且,仅凭借一个令人发笑的鼓风机,却产生了吹过茫茫沙漠的巨大的生命之风。这种技术的粗浅与大自然的威力、那位具有呼风魔力的风婆和这位充满想象力的老电影人相比,实在显得微不足道了。影片的主题不再是人类战胜自然,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影片最后那老妇人和老头儿在风中开心地笑了,风,在影片中发挥了创新者、过滤器,以及变革者的作用,它继续吟唱着运动之歌。老头儿在风中站起身来,缓缓地消失在地平线上。
坚定而平静。
[1] 引自伊文思于1925年1月14日写给梅普·巴尔格里·格林的信。Collection Miep balguerie-Guérin,伊文思欧洲基金会,奈美根(Nijmengen)。
[2] 同上,1926年11月10日,MBG/ESJI。
[3] 尤里斯·伊文思在奈美根博物馆“Commanderie van Sint Jan”展览开幕式上的讲话。参见Rondon Joris Ivens, wereldcineast 1898-1934, 16 November 1988.
[4] L.J. Jordaan著《尤里斯·伊文思》,Amsterdam-Het Kompas,1931年出版,第5页。
[5] 同上,第11页。
[6] 详细信息请看Urias Nooteboom和本文作者Andre Stufkens合等的《De bron, De familie Ivens en Joris Ivens jeugd in Nijmegen》,in Rondem Joris Ivens, wereldcineast 1898-1934, pp12-32, Het wereldvenster/nijmegen Museum 'Commanderie van Sint Jan'1988, The C.A.P Ivens are in the Municipal Archives of Nijmegen.
[7] C.A.P Ivens, manuscript 'De fotografie in de laatste veertig Jaren’, Nijmegen 1927, written for Veertig jaren folografie, gedenkboekje der NAFV 1887-1927, Amsterdam 1927.
[8] ProvinciaIe Geldersche Nijmeegshe Courant, nr. 102, 1917年5月2日。
[9] 同上,1917年5月5日。
[10] Photo albums in the Collection Nooteboom-Ivens, Den Bosch.
[11] Typed report in response to article by W.H. ldzerda, 'Herinneringen’, Joris Ivens Archives/ESJI Nijmegen.
[12] L.J. Jordaan著《尤里斯·伊文思》,Amsterdam-Het Kompas,1931年出版,第5页。
[13] 伊文思、罗贝尔·戴斯唐克著《一种目光的记忆》,1983年出版,第66页。
[14] 1907年2月20日,基斯·伊文思在“宗教与科学”的第一个5年计划上的讲话,见伊文思基金会卡皮档案收藏。
[15] C.A.P Ivens and others, Gedenkboek voor de Waaloverbrugging, Nijmegen, 1936.
[16] L. J. Jordaan著《尤里斯·伊文思》,Amsterdan·Het Kompas,1931年出版,第5页。
[17] 1986年5月7日,汉斯·舒茨对伊文思的采访。
[18] 引自伊文思写给梅普·巴尔格里·格林的信,日期不详,落款“周二的晚上”。
[19] H.C.L.Jaffe, De Nederlandse Stijlgroep en haar sociale utopie, Amstedan Meulenhoff, 1986, p126.
[20] 引自La vie mène la danse,为非正式出版物,是Germaine Krull的自传。
[21] 1935年,尤里斯·伊文思发给莫斯科的一份演讲手稿。伊文思欧洲基金会收藏。
[22] 引自伊文思写给梅普·巴尔格里·格林的信,I,1922年11月1日,寄自Schoneberg-Berlin。
[23] Herndrik Marsman,1926年5月20日写给Elisabeth de Ross的一封书信。
[24] Walter Benjamin in “Kleine Geschichte der Photographie”, 1931.
[25] 见汉斯·舒茨著《危险地活着:伊文思传》,1995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第54页。
[26] 见汉斯·舒茨著《危险地活着:伊文思传》,1995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第55页。
[27] Menno ter Braak, Cinema Militans, De Gemeenschap, Utrecht, 1929.
[28] 伊文思、罗贝尔·戴斯唐克著《一种目光的记忆》,1983年出版,第66页。
[29] L.J.乔达安著《尤里斯·伊文思》,Amsterdan-Het Kompas,1931年出版,第10-11页。
[30] 1927年6月8日,尤里斯·伊文思写给亚瑟·雷宁的书信。
[31] Joris Ivens, Autobiografie van een filmer, Born Publishers, 1970, p28.
[32] 伊文思《先锋纪录电影笔记》,见Rondom著《伊文思:1989-1934》,第180页。
[33] 伊文思《纪录电影的创作方法》,见本书第三部分同名文章。
[34] 同上,见本书第三部分同名翻译的文章。
[35] Basil Wright, The Long View,伦敦,1974年第117页。
[36] 约翰·范·德·库肯在尤里斯·伊文思展览开幕式上的讲话,发表于Film and TV maker,nr.289,阿姆斯特丹,1989年。
[37] 尤里斯·伊文思《法西斯与电影》,发表于Links Richten, nr.8, 1931年5月1日。
[38] 巴兹尔·赖特《长远的观点》,1974年,第117页。
[39] 约翰·范·德·库肯在尤里斯·伊文思展览开幕式上的讲话,发表于Film and TV maker,nr.289,阿姆斯特丹,1989年。
[40] 伊文思《法西斯与电影》,发表于Links Richten第8期,1933年5月1日。
[41] 布莱希特《辫证的戏剧方法笔记》,引自《布莱希特政治的戏剧实验》SUN,奈美根,1972年,第32页。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